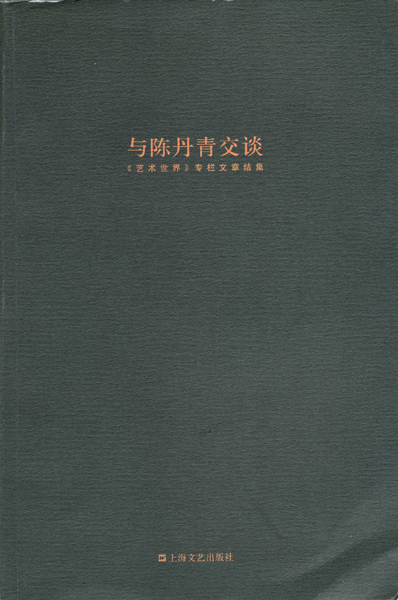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讽人嘲己成文章 ——读《与陈丹青交谈》 ( 返回 )
这册小薄书是陈丹青十二次答读者问的记录。话题来源很广,取自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大的范围是关于艺术,也有教育;回答则完全随意,不求标准答案,只把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端出来,与读者分享。交淡的文章最初发表在《艺术世界》杂志,然后结集出版,“读者”的范围便有了扩大。不管哪样读者,都会有种现场感,置身那种对话的气氛中,仿佛可以亲自参与。《与陈丹青交淡》提供了一个范本,让对话进行得深入且有趣,不是一方作导师状另一方洗耳恭听,也不是你问你的我答我的形成两张皮。 我想秘诀在于陈丹青的诚实,放下架子,把自己摆在与读者对等的地位上。这份诚实里也包含着他的聪明,不追求四平八稳,带点棱角,给人留下回应反驳的余地。于是对话可以不断进行下去。 乍看上去,陈丹青有点玩世不恭,仿佛仗着自己在国外呆过一些年,回国后就可以肆无忌惮,指东道西。其实不是的,可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很有分寸,就是追求这么痛快地说。笔谈毕竟不同于说话,有个后期修改的过程,可以对观点措辞进行把关。陈丹青的文字不套用官方的空话大话,追求文字的质感和丰富表现力。他说,评论艺术何必总用“好坏”,可以改成“良莠”、“高低”、“雅俗”、“文野”、“巧拙”等。前面读到一家周刊上的文章说向陈丹青学语文,此言不虚。思想得用语言来承载,富有奥妙的观点用干枯陈朽的文字表示出来?怎么能想象。 陈丹青的文字放得开又收得拢,时时展现出一种纵横捭阖的气象。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不假装正经,既讽人又嘲己,在嘲讽之间向读者传递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一月月读下来,只觉通体舒畅,怎一个“爽”字了得。 你看他对感叹“青春无悔”的老三届多么无情,把“可怜人”、“倒霉鬼”都用出来了。这未必周全,人家要是真的无悔呢?不过他也可以成一家之言,给那些准备为青春唱赞歌的老三届提个醒儿。三大男高音到故宫演出,一批老树为此遭殃。陈丹青说的是:“劈倒故宫的几棵树,算个屁事!”何其直率也,好像在自家客厅里一样,毫无遮拦。树已经被毁了,平缓的劝言有什么用?劝了又有谁听?不如这般讥讽来得痛快。至于对外语考试的批判,则是愤激得几乎毛发倒竖了:徐悲鸿林凤眠得呈交四六级外语分数才能在境内报考油画专业,梅兰芳侯宝林李连杰收徒之前须过外语关——何其荒唐乖谬!“大病既久,仿佛无病”,和颜悦色的建言不济事,只好作这般无奈的疯话。陈丹青心里一定是明白的:就算这套万恶的考试制度一时纹丝不动,还是值得发出响音来震它一震;总会有那样的日子,英语从教育大堂座上宾的位置退下来,呆到合适的地方去。 至于自嘲,那就更多了。陈丹青可能觉得那就是自己说话的方式,并不当作“嘲”。比如,自认为是老盲流,写评论不希求别人相信,被女儿喝令滚出房间,看到乡村医疗手册上的窈窕淑女体型时血脉贲张,出国之时即自我淘汰主动出局,当着教授仍自认是个学生,诸如此类。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很低:平常的写作者,没什么威严的父亲,有不太安分的欲望,不认为自己画画多高明。作为一种说话的策略,把自己放低了,不容易给人留下把柄,进退自如;想到陈丹青在其他作品里的行文风格,还有他演讲的风格,可以知道这份低调也是他的为人方式。他就是这么个人,有真知灼见,看上去却不太当回事,洒脱得很。可以说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了,跟他喜欢的鲁迅有点像。 诸位看官一定会有同感,《与陈丹青对话》的底色是真诚。他把读者当回事,有时候一问一答结构明确,后来却完全融合到一起去,推心置腹。书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坚持对话很不容易。陈丹青艰难地谈了一年,以后不想再来了。书的出版实在大有功德,带给读者一些与艺术有关的见解,也叫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种识见不俗却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2009-3-30
《与陈丹青交谈》书影 【关于陈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