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邂逅贾樟柯
( 返回 )
(一)
大约在2004年冬天,我第一次看了影片《小武》。不知因为当时正犯困,还是因为它天生具有催眠的本领,我居然晕晕乎乎睡了过去。 时过境迁,当我在两年后再次看完《小武》的时候,不禁暗暗感到愧疚,因为我发现当初自己冤枉了这部内秀的影片。故事本不是重点所在,它用舒缓的节奏描画了一个人,不瘟不火,并由此展露一种生活方式。《小武》告诉人们,乱糟糟的背景下生活着时代的边缘人,虽然不苟言笑,却别有温情。 实在太可爱了,这个自称手艺人的扒手梁小武。已变身为知名企业家的昔日同伙小勇没把将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他,接着又拒收他来路不正的礼金,这让小武大为恼火。无奈归无奈,他的社会活动空间还是一点点被挤压了。歌厅小姐胡梅梅的不辞而别又一次让他感到失落。朦朦胧胧的感情,似乎和那份礼金一样上不了台面,脆弱而不堪一击。影片最后,被铐在路边的小武蹲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知如何面对慢慢聚拢的围观的人群。 正像罗大佑歌曲里唱的那样,“野百合也有春天”。现实中的小武们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而社会在有意无意间把他们忽略了。贾樟柯做了切己的处理,用平静的镜头语言表达出小武的追求和困惑。观众不会因为他职业的不体面而产生嫌恶的情绪,相反,会从心底涌起一种温暖的认同感。“严打”,街头录像店,卡拉OK……都是那样的似曾相识,如在身边。哪怕是对导演所知甚少,我也可以大胆地推测:他一定熟悉小县城的环境,并且对那种非主流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 《小武》闪耀着一种掩不住的才华,荡人心胸。单是因为它,我也觉得贾樟柯这位导演很可期待了。
(二)
或许是老天爷跟贾樟柯开了个玩笑,他最初的几部片子是被封杀的,构成“故乡三部曲”的《小武》、《站台》、《任逍遥》无不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贾樟柯一步步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世界》得以公映,进入正常的电影市场。当《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时,贾樟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导演实力,让世人刮目相看。 当然,得奖只是外在的,影片究竟会带来一种怎样的体验,观众还是要看了以后才知道。《三峡好人》平行讲述了两个与寻找有关的故事:韩三明寻找分别十六年的前妻,最后他们破镜重圆;沈红寻找两年未见的丈夫,最后他们劳燕分飞。故事本身算不上曲折离奇,影片的动人之处在于故事的展开过程,里面延续着贾樟柯电影的一贯风格——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和对普通人感情的展现。 韩三明是位老实巴交的矿工,不善言辞。面对陌生或熟识的一切,他镇定又沉静,带着几分木讷,好像比飞速前进的时代慢了一个节拍。影片用平实而诙谐的语调叙述了这位小人物的生存智慧:给船老大送酒,为小马哥点烟,在诈钱的魔术师搜身时不动声色地掏出弹簧刀。当他拿着五十元纸币说“我家的风景也在钱上”时,观众又不由得为他的淳朴善良所感动了。韩三明同时是一位行动者,千里迢迢从汾阳赶到奉节,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那种力量如同江水一般,看上去很平静,实际却急流涌动、滚滚向前。
相较而言,导演在沈红身上着墨似乎少一些,表达更为含蓄,人物形象不如韩三明那般厚重;不过她自爱又自信的性格依然是可触可感的。沈红若无其事地打听 三峡工程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新与旧在碰撞,破坏与建设同步展开,消逝和崛起相互更迭。除了墙头标示的156.3M水位线,贾樟柯更多地用小人物、小场景表现了这个时代的沧桑巨变。染着一撮黄毛的摩托车司机说:“一个两千年的城市,说拆就拆了。”他家曾在如今轮船的下面,青石街5号同样已经被江水所淹没。韩三明问他为什么不早点说,黄毛司机轻描淡写说道:“又不是我让淹的。” 外来文化影响着古老的县城,小马哥的出现加重了影片的惆怅气氛。他学着港台影视剧的样子,潇洒地扯一张纸烧着了用以点烟,还对打火的韩三明说:“做兄弟的,我一定会罩着你。”以周润发为偶像的小马哥最终却被群殴致死,正像港台剧里的倒霉蛋一样,让人不胜唏嘘。韩三明又一次为他点燃香烟,致以无言的祭奠。从这不显山不露水的镜头语言中,可以看出贾樟柯内心最柔软的那部分:一方面是对韩三明的敬重与激赏,一方面是对小马哥的怜惜和同情。他的心是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充满了人文关怀。 船头歌舞厅里赤膊的光头男人声嘶力竭地高吼《酒干倘卖无》,扭动身子向观众搔首弄姿,如同走红的三流歌星一样;穿行在断壁颓垣间的小男孩用稚嫩的嗓音唱起“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那么动情,那么投入,那么忘乎所以。贾樟柯毫不吝啬地给这些演唱者以长时间的镜头,用歌声把影片里的人物和现实的观众紧密联接在一起。 我是笑着看完《三峡好人》的,影片结束时,我却有种想哭的感觉。
(三)
很久以来我都认为,菁菁堂是一个福地。我曾在这里参加第三代导演谢晋的《女足九号》首映式,见到第五代导演吴子牛和《国歌》的剧组人员;而这一次,我又在菁菁堂和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贾樟柯有 影片放映结束后,贾樟柯走向前台。他下身穿着深色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灰白色的外套,风尘仆仆,好像刚刚从拍摄现场回来。没有煽情的问候,没有铿锵的豪言壮语,他接过观众献上的鲜花,用温和的语调与他们展开了对话。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贾樟柯的电影并没有因为被禁映而失去观众。提问的同学中,有的在四五年之前就已开始喜欢他的影片,有的放弃了招聘会专门赶来参加首映式。活动结束后,两名女生尖叫着冲向前台去合影留念。贾樟柯一点大牌导演的架势也没有,耐心地签名、合影,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目睹这一切,我看到了一位成功者所具备的谦逊品格。 在贾樟柯的眼里,三峡是一个江湖,刘备来过,李白来过,很多当代人也来过。江边是飘泊不定的码头,每天都有物资的交流。因为三峡工程,上百万人移民到了别的地方,生命的轨迹随而改变,为时代进步承担了巨大的代价。他为这些普通人感动,所以把镜头对准了他们。贾樟柯以这片江湖为舞台,讲述两个人的故事。在感情的世界里,他们都是漂泊的人,一直在寻找归宿;最终他们作出决定,为自己的幸福找到了出口。他说:“人不是哭着生活的,虽然艰难,还是要乐观地去面对。对这两位主人公而言,不管复合还是分开,都是一种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是行动。韩三明通过选择找到了幸福,沈红通过选择赢得了尊严,行动的精神是一致的。” 贾樟柯在三峡这样宏伟的背景上展开他的故事,还善于从烟、酒、糖、茶的细节中折射时代的精神。他去过拆迁工人的家,那里一贫如洗,没什么值钱的家什。窗台上一个落满灰尘的“山城啤酒”空瓶子让他产生了不尽的联想:那是过生日的一次奖赏,还是春节时客人带来的礼物?贾樟柯把《三峡好人》的英文名字定为“静物”(Still Life),而静物正是被忽略的现实。他感慨说,人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打开心扉去接受另一种现实。一块大白兔奶糖,两个人分了吃,贾樟柯乐于表现这种简单的幸福感。他觉得烟酒糖茶中包含着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的印迹,由此可以联接现实和历史,讲述现代人的生存境遇。
从《小武》的汾阳到《三峡好人》的奉节,贾樟柯喜欢把故事放在县城里,有人说他对小县城的诠释特别有味道。贾樟柯坦言,自己正是从小县城走出来的。他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21岁外出求学前一直生活在那里,年轻时候 对贾樟柯来说,电影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是超越了文字的艺术。一个人走在三峡,他感受到了孤独的压迫,期望外星人能给他陪伴。于是,《三峡好人》中出现了飞碟,给徘徊不安的沈红以精神的慰藉。因为钱不够而只建了一半的移民纪念塔矗立在江边,奇丑无比,他觉得很不协调,于是在影片中让它腾空飞走。故事末尾还出现了走钢丝的场景,或许也包含着在平衡中艰难前行的意思吧。 经历过十几年的探索,贾樟柯的表达还包含着超越了个人情绪释放的更为深远的意义。他是一位执着的行动者,像韩三明那样没脾气而有主见,像沈红那样外柔内刚;他又是一位宽厚的仁者,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关注普通人,通过影片表达沉在心底的悲悯情怀。看过影片,又在现场感受了贾樟柯的风采,我不由想:他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大奖,这是值得的。
(四)
见面会结束后,很多同学还是团团围着贾樟柯,助手好不容易才把他“解救”出来。作为一名学生记者,我很希望能与他当面交流;可他一直忙于宣传新影片,非常疲累,我又不忍心再麻烦他。最后是宣传部的老师促成了这桩好事:贾樟柯没有直接离开,而是回到贵宾室,接受了我的采访。 贾樟柯坐在东边的长沙发上,我坐在南边,各自靠近沙发的边沿;两人都略微歪了身子,相隔三尺,对面而坐。哪怕已经很累,他脸上还是流露着亲切的笑容,我感受到了一种叫做涵养的东西,心情也变得舒缓起来。 《小武》中出现了《心雨》、《爱江山更爱美人》等流行歌曲,《三峡好人》里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同样大俗大雅,带给观众心灵的震颤和共鸣。我问他,这样处理是不是有什么意图或期望?贾樟柯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过深入的考虑,娓娓道出了个中原委:这么做是有意为之,因为流行歌曲(包括网络歌曲)是非常私人化的表达,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欲求;放在影片里,歌曲与人物的需求相一致,可以给他们带去短暂的快乐。他还说,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歌声中得到抚慰或逃避;观众的心随剧情流转,于是容易受到流行歌曲的感染。
每当有观众进来请求合影,贾樟柯就会愉快地满足他们;拍照结束了,采访便继续下去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我对受访者还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此前已经打过很多交道。这可能是因为他为中国移动拍的那则广告吧。贾樟柯把镜头对准了在椅子上倒立的小女孩、缓缓移动的城市列车,最后是自己坐着摇臂升到高空。他旁白道:“以前我说拍电影,他们说笑话。不管别人怎么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相信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我能。”广告简短而含义深刻,每次在电视里看到它,我心中都有一种升腾的感觉。眼前的嘉宾便是广告的主角,一样的和蔼,一样的含蓄,一 三峡是当代中国脉动最强的所在,如果加上影片里提到的司空见惯的煤窑矿难、港台剧对各色人等的深刻影响,似乎可以看出《三峡好人》在记录时代面貌方面的意图。我问他:“在导演这部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为时代立言?”贾樟柯回答道,中国正处在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峡工程是一个缩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确实再现了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三峡好人》却未必能做到。随后他又笑着说:“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应该力求准确地反映这个时代的面貌吧。” 我对这次采访感到非常满意。起身离开贵宾室的时候,我想起了上升的摇臂,便跟他说:“我经常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看到你的广告,听到‘我能’的时候,总是觉得很豪迈。”贾樟柯拍拍我的肩膀说:“嗯,相信自己,你也能!”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个子并不高,可是有一种非常坚定的力量,像一位可亲可敬的兄弟,叫人觉得友好又实在。 这天是2006年12月7日,星期四。两天之前,贾樟柯去过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文汇报》、《新闻晨报》以及《新民晚报》等都有报道。我曾和别的学生记者联合采访韩剧《大长今》的导演李丙勋,而这次是代表《上海交大报》独家专访一位知名导演,委实不可多得。我崇拜有才华的人,贾樟柯的影片和谈话让我大觉快慰。我乐意记下这段愉悦的经历,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2006年12月10日--12月14日
(首次发表于2008年1月总第10期《表达》。责任编辑:石莎莎。查看杂志情况请按这里。 转载于2008年3月24日《上海交大报》第4版。编辑:杜欣。 前三张图片来自网络,后三张图片的摄影为武新民老师。)
相关联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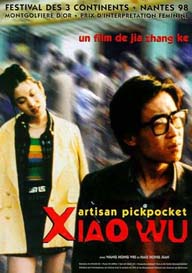 过后回想起来,除了含混的对白、嘈杂的广播以及一个架着眼镜穿着西服的年轻男人以外,脑子里几乎没有留下别的印
过后回想起来,除了含混的对白、嘈杂的广播以及一个架着眼镜穿着西服的年轻男人以外,脑子里几乎没有留下别的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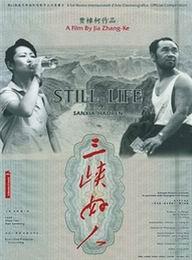 丈夫有没有和别的女人相好,谁知道当时她心底涌起了怎样的波澜?她安然接受丈夫无心于婚姻的严酷现实,和他在江边的乱石前跳了一支舞,而后毅然离开,不再回头,就像一锤敲开生锈的铁锁那样干脆利落。没有哭泣,没有抱怨,在一路寻找中,沈红失去了爱情,赢得了尊严。
丈夫有没有和别的女人相好,谁知道当时她心底涌起了怎样的波澜?她安然接受丈夫无心于婚姻的严酷现实,和他在江边的乱石前跳了一支舞,而后毅然离开,不再回头,就像一锤敲开生锈的铁锁那样干脆利落。没有哭泣,没有抱怨,在一路寻找中,沈红失去了爱情,赢得了尊严。 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三峡好人》全国公映前,贾樟柯穿行于各大高校做推广,上海交大也是其中的一站。
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三峡好人》全国公映前,贾樟柯穿行于各大高校做推广,上海交大也是其中的一站。
 。《三峡好人》的片名里包含了两个要素,
。《三峡好人》的片名里包含了两个要素, 样的坦诚。
样的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