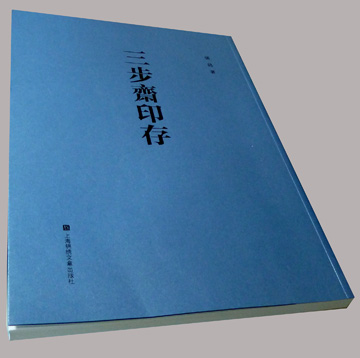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张铭之变 ——《三步斋印存》读后
通览《三步斋印存》,不难发现张铭在文字运用上有一个特点:善于运用短小精干的文字表达创作体会及艺术追求,而非进行系统化的长篇大论。一则则创作手记自不待言,轻快凝炼 且言之有物;序言用十一条札记来代替,长则数百字,短的只有几十字;后记略有篇幅,记录成书过程,也不过八百来字;集中表达个人篆刻观点,是借助于友人的提问。张铭不是没能力撰写长文,他为《韩天衡印谱(2004-2008)》作的序言即有足足五个页码,立意独到,论述周详,笔记体的论艺风格可以显示张铭对待自身创作的一种态度——作品是第一位的,应当更多地让作品说话。 响鼓不用重棰,这些片断化的文字如实记录了三步斋主领异标新的艺术追求和避同求变的发展轨迹。张铭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游走于传统与先锋之间,在市场需求与个人热望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牵引下艰难前行。《三步斋印存》是他近几年变法的成果展示,不仅在他本人艺术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这种探索融入篆刻艺术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成为值得书写的一笔。 面对三步斋主的一百四十方篆刻新作,普通读者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风格太狂了,用刀细碎,线条生涩,没什么意思。一名对书画篆刻感兴趣的藏家,如果眼前有个机会,只能收藏张铭的一方印章,那么他很可能选择选择工稳细致的那一路,因为不论是鸟虫篆还是满白文,张铭都刻得非常漂亮,既中规中矩又趣味昂然。如果藏家把书中收录的一方写意古玺印拿给其他人看,很可能得来这样的议论:“有什么好看的,一个初学篆刻的印人,随便刻刻就是这种效果了!”简而言之,张铭的新腔探索远非人人说好,会遭遇一般藏家的忽略甚至排斥。 对此,张铭和认可他艺术选择的人大可不必担忧。真正的先锋艺术必然是小众的,艺术家以离经叛道的姿态登上舞台,赢得少量喝彩的同时,往往遭遇抵制和责骂。他们激荡现有格局,实际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潮的作用,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变得大众化,最终沉淀为艺术传统的一部分。就像19世纪后期的法国印象派绘画,当初为“主流”画展落榜者的聚会,被冠以嘲讽性的“印象”之名。这群艺术家以大量取材自然、表现光影律动、注重瞬间感受的开创性进入历史,由边缘而中心,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 印记。 作为一名以刻谋生的职业印人,张铭的选择是“两条腿走路”,即一部分精力用来刻工稳印,适应市场需求,另一部分精力创作写意印。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张铭古玺风格的创作在社会上接纳能力有限,他仅仅靠此无法 维持生计。 篆刻家张铭的不俗之处,正在于他的“两条腿走路”。作品入选诸多书法篆刻大展、出版《张铭鸟虫篆印谱》等专著之后,张铭没有躺在原有成绩的温床上睡大觉,沿袭四平八稳的印风迎合藏家喜好(那样他的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而是磨平得意之作再上路,在刀石冲撞间寻觅全新的艺术表达的可能性。由此,篆刻于他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心性的流露,在他的生命中有着极重的分量。《三步斋印存》的成书是张铭不安现状、上下求索的阶段性答卷。 这份答卷能够获得怎样的分数,观者自然见仁见智,击节赞赏或弃如敝屣,都不足为怪。本人也曾纠结于大贬大褒两种极端的评价,困惑不已。几天来渐渐领悟到,新风格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可以在直观感觉上不喜欢张铭的新腔,但是,值得为他的变法勇气鼓掌,尤其值得对其古玺风格日益扩大的影响树立信心。 在论及先锋艺术家对艺术传统的反抗时,西班牙哲学社会学家奥尔特加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艺术家要么与过去一致,并把过去视为自己的财产,这也使他感到一种使传统不断完善的号召力;要么,他会发现自己对通常被夸耀的过去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无穷厌恶。在前一种情况下,艺术家乐于落入传统规范并重复某些神圣的模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不但会偏离业已确立的传统,而且同样乐于阐明自己的作品对由来已久的规范提出质疑。”( 转引自周宪著《20世纪西方美学》,第45页)毫无疑问,张铭正是后一种艺术家,他以自我否定的姿态开辟新风,让传统篆刻艺术呈现出先锋性的一面,其革故鼎新之功理当为 篆刻史所铭记。 篆刻自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艺术上不断演进,在秦汉与明清形成了两座高峰。艺术家要开宗立派、超越前人迈出新的步伐,极为困难。这非但需要创作者渊博的知识积累,广采众长,而且必须有弃旧向新的志向,持续付出艰辛的劳动。 诚然,好的艺术同样需要灵感,它不是凭空飞来,一定建立在扎实创作的基础之上。张铭在问道于韩天衡先生期间,在参加当代中青年篆刻名家演习班期间,在撰写《篆刻三百品》词条期间,都有过相当厚实的研究与实践储备。 张铭取法秦汉战国古玺,融入个人的思索与创造,篆法尚古、章法主散、刀法求拙,境界大开大合,终成自家面目。 如果把《三步斋印存》与斋主参编的《篆刻三百品》比照来读,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判断:张铭的新作风格和历史上诸印家不一样,他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这种“独特的东西”可能只有一点点,却是张铭数年变法收获的财富,也是他为推进篆刻艺术做出的可贵贡献。有的艺术家只是为满足市场的 庸俗爱好而模仿前人、重复自己,试想,未来篆刻史上怎么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同样,如果张铭只是安于吃以往鸟虫篆的老本,悲观地看,若干年后他很可能在老师韩天衡巨大光环的映照下黯然失色,变得籍籍无名。 品赏三步斋印作,但觉古风拂面,生气盎然。 张铭篆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运刀石充满了激情,快速成印,最终印面呈现出张扬灵动的风貌。构思之后急速运刀击石,三下五除二,甚至只需七八分钟即能完成。细究起来,这种迅疾远非不假思索的随意冲切,而是在盘思多时甚至数易 印稿之后,胸有成竹的流畅表露。其中常常含有即兴的成分,化为作品的天然之趣,烂漫可喜。 把目光放得更开阔一些,不难发现篆刻艺术在近世的一种转向,即从精雕细凿的慢刻转变为大刀阔斧的快刻。齐白石单刀立就,开风气之先;当代部分篆刻家光大此艺,如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徐庆华冲刀急奔,线条具书法之意,性情饱满,才情外现。三步斋主加入了“激情篆刻”的大合唱,下刀果敢猛利,尽显豪放之气,成为印风转变的有力推手,这凸显了张铭变法于印艺走向的宏观意义。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篆刻家 沿此方向继续尝试,带来快刻风格的整体勃兴。 再回头看《三步斋印存》里的笔记文字, “缺乏自我意识的创作都是毫无意义的”,显示出张铭的艺术追求朴素、明晰而坚定。 新作得以付梓,因为时隔三年,他对以往出的篆刻作品集“感觉不太满意”,以至形成一个“心结”。先行者需要直面寂寞,艺术市场上乱象丛生,他坚持工刻主外、写意主内,“而不会改变自己的审美格调”。艺路探 步难且痴,张铭配得上真正篆刻艺术爱好者的掌声,也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人们会重新审视这位孤独而执著的远行者,并献上崇高的敬意。
2012年12月15日于素槐山房
转载:张铭博客
《三步斋印存》书影。2012年10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