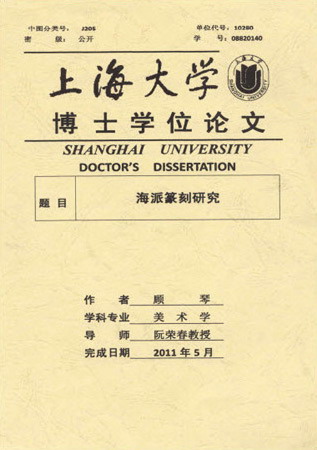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开宗立派建奇功 ——顾琴博士《海派篆刻研究》读后
“海派”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汇,大至“海派文化”、“海派艺术”、“海派风格”,小至“海派文学”、“海派书法”、“海派绘画”,早已进入了艺术家、作家、评论家等的学术表达乃至日常对话。一般而言,“海派”与上海的城市精神相关,如海纳百川、崇尚创新、新潮时尚等。“海派篆刻”的表述也不时见诸图书报端,但往往是出于使用语言的惯性;至于作为艺术流派的“海派篆刻”拥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怎样的形成发展过程,长期以来乏人问津。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顾琴历时三年完成博士论文《海派篆刻研究》,填补了这片学术空白。 论文从海派篆刻的社会学观照入手,概说上海华洋杂处、文人交汇、社团纷起的时代环境;继而分析海派篆刻的商业特质,阐明艺术市场与艺术流派之间的互动关系;接着转入探究海派篆刻的文化性格,在传媒出版业繁荣的同时,海派篆刻研究涌起清醒的主体意识,研究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最后聚焦海派篆刻的艺术风格,以吴昌硕、赵时棢、王福厂、简经纶、钱瘦铁、来楚生和韩天衡等七位篆刻家为个案,在田野考察式的探访赏鉴中呈现海派篆刻的总体艺术面貌。时代环境——商业特质——文化性格——艺术风格在逻辑上层层深入,由外部转向内部,如同剥洋葱一般步步逼进研究对象的内核。这完全符合人们的认知与接受习惯,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具备了雄辩的说服力。 “海派篆刻”的孕育生长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既没有总体性的宣言主张,也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创始人。顾琴博士在大量史料中归纳剔析,对“海派篆刻”划定边界、明确分期,给这个本来模糊缥缈的概念赋形凝神,成为“海派篆刻”开宗立派的研究者,功绩 奇伟卓著。论文最核心的内容当数对海派篆刻艺术风格的探求开掘,占据了正文一多半的篇幅。作者在对社会文化背景、近代篆刻发展历程宏观把握的基础上,深入每个艺术家作品的内部,写出各自“这一个”的艺术特色。从吴昌硕的浑穆渊雅、自然冲淡,到来楚生的错落天真、形式现代,直至作为海派篆刻“新的领军人物”韩天衡的雄浑、华美、超逸,堪作一部提纲挈领的上海篆刻风格简史。作者探幽寻胜,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发前人之所未发,学术洞察力、艺术鉴赏力皆于此清晰可见。 在探析来楚生印风一节,无需讳言,顾琴博士倚重张用博、蔡剑明著《来楚生篆刻述真》一书,从中得到了来氏篆刻观念、形式语言、生肖印图式特点等的大量研究资料。《来楚生篆刻述真》由上世纪80年代的《来楚生篆刻艺术》补充深化而来,在来氏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地位。顾琴博士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不是把张著的现成观点简单移植到论文中,而是取其原始资料和初步赏析,服务于自身的学术论断。张著原从虚实、统一调和、呼应、随形布局、对称重出与平行线的破除、移位屈伸及合文六方面阐释来氏章法风格,但顾琴博士认为他“对来氏印风之形成独特性的理解还是很模糊不清的”(第134页),以现代形式构成的视角重新审视,围绕逼边、并置、纠缠于入侵、支离——陌生化、向线落刀等五方面加以阐述,虽然部分论述带有张用博先生的影子,但整体架构是全新的,对来氏篆刻风格提炼也更加精当,显现出青出于蓝、后来居上的优秀品格。对生肖印图式特点的分析同样如此,“汉画像石式车马人像图”和“老奶奶上夜校”两件印作在张著皆有出现,分别为来氏汲古再创作、涉足民歌题材的例子,顾琴博士则从线条印化成为“印画”的角度去解读,新意立现。对于张用博先生关于“多形生肖印为来氏首创”的观点,尽管很重要,因无法与来氏“形式现代”的主题 有效对接,顾琴博士便弃而不谈,其“为我所用”的自主研究意识跃然纸上。 顾琴博士对海派篆刻艺术风格的剖析精微入里,对此艺术流派商业特质、文化性格的梳理寻觅同样多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市场流通、新闻出版业发展、社团活动等对于流派形成、艺术家脱颖而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吴昌硕润例比较高,不光因为他倡导篆刻变革,还有赖于王一亭等人的宣传,其“市场价值,是广为宣传的结果”(第34页),媒体传播、名人介绍等都推动了书画艺术品市场的发达。作者在比较不同篆刻家的润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印章的价格并不全是按其艺术性的高低定的,而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则而变化的,艺术品的价格与艺术品质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完全以市场运作的规律进行。”(第57页)当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金钱对创作主体性逐渐丧失的腐蚀作用,这些分析对于认识当今的艺术品交易和篆刻创作不乏现实参考意义。 《海派篆刻研究》的五个关键词分别为海派、海派篆刻、创新性、多元化、现代性,阅读之初不免对作者阐发“海派篆刻”的风格特点有所期待——正如后三个关键词所提示的那样。读完论文,不由生发意犹未尽的感觉。第五章《海派篆刻的风格学关照》前言中,作者承认“海上印人虽来自各地,有不同的师承,但又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一风格流派的作品中都有某种共同的形式因素”,创新性、多元化、现代性的风格概括呼之欲出 。令人备感意外的是,作者援引美国艺术史家阿诺德·豪塞尔的观点宣称“只存在各种具体的风格而不存在抽象的风格”(皆见于第85页),主动放弃了以某种共同的东西总揽整章内容的努力。读者不禁要问:上文刚说过海派篆刻有“共同的特征”,那到底是什么?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不是自相矛盾吗?相对于154页正文拿出84页谈七位篆刻家艺术特色的用心安排,本来份量极重、堪为整篇论文承上启下之枢纽的第五章序言却只有半页多篇幅,未免显得寒酸 、太单薄。大量出现的阿诺德·豪塞尔的话更像是作者偷懒的借口。与此相应的是,其后海派篆刻个案研究侧重于彼此独立的呈示,缺乏一种横向间的比较 联络。这项薄弱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于,七位海派篆刻代表人物成了七座孤立的山峰,而没有被“共同的特征”连成一片高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全篇论文的品质和成色。 顾琴博士把“海派篆刻”的时间边界定为晚清到“文革”结束,将韩天衡视为“海派篆刻终结的代表人物”(第45页),相当于把“海派篆刻”判了死刑,认为其只应存在于历史的回顾之中 。这是值得商榷的。从研究便利角度考虑,如此处理未尝不可,毕竟,研究对象的边界如何划分属于学术主张的一部分;然而,从当前人们对“海派”及“海派篆刻”的亲近心理来说,把“海派篆刻”说成“过去时”的艺术流派却未免恰当。2012年朵云轩春季及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均设置“当代海派名家篆刻专场”,“海派篆刻”的表述在传媒评论界频频出现;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为“2012年上海篆刻邀请展”撰写序言,其中也 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当代海派篆刻”的提法。顾琴博士论及的七位篆刻家之中,韩天衡的篆刻创作力依然旺盛,他的一批学生已卓有成绩,来楚生弟子童衍方、张用博等师承有序者也都活跃于印坛,与海派篆刻的传统一脉相承。“海派篆刻”依然生动鲜活,宜于视作开放的、未完成的、正在进行的状态,由此更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和感情期待,并为“海派篆刻”赋予时代的 全新内涵。 《海派篆刻研究》为顾琴就读于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时的博士论文,2011年5月完成,当年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即将付梓。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相信专著的出版将成为新的开端,不仅为顾琴博士奠定 海派篆刻研究第一人的稳固地位,还将给其他学者关注解读海派篆刻乃至海派艺术、海派文化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2013-1-11
《海派篆刻研究》封面。论文收入中国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