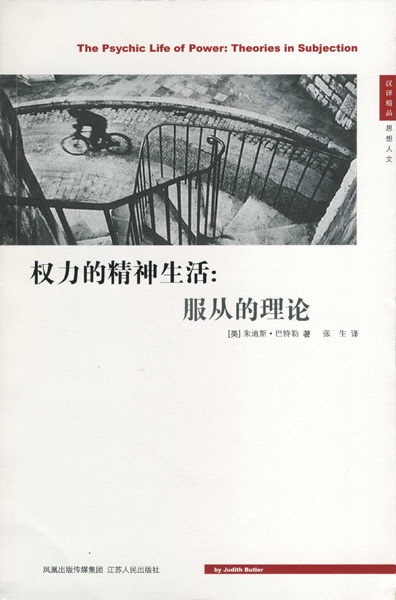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啄木鸟 ( 返回 )
座谈会进行得相当拖沓。我硬撑到结束,已是十二点多。算上2001年听余秋雨演讲和今年早些时候看望张老师,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同济大学了。当然,参加座谈会只是一方面,我更在意的是找张老师聊天。 一从逸夫楼出来我就打电话,张老师说在食堂,叫我直接上三楼找。到了一看,他正吃饭呢,不期然马纶鹏坐在对面。我拿了张老师的饭卡,去买了一份饭。 马纶鹏是年龄比我小的师兄,勤于学习且成绩优异,从交大毕业去美国读博士,已经念过三年,这次回来休假。在张老师的安排下,他要给同济中文系学生上课,进行电影理论方面的研讨。可以想见,等过两年毕业, 马纶鹏也会像张老师这样,走一条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路。在大洋彼岸,马纶鹏经常浏览交大主页,了解学校的最新发展。张老师笑着说:“我从来不看交大主页,因为我知道交大没有发展;我也不看同济主页,因为我知道同济的发展都在我这里。” 吃完午饭,我们去综合楼里的咖啡馆。这里环境清幽,咖啡是现磨的,又浓又香,坐下来聊天十分惬意。马纶鹏在美国晒得厉害,回来环境一变就不适应,眼角皮肤有点胀裂。张老师说那是日光性皮炎,当初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访问学者,也受过日晒的苦头。他向马纶鹏介绍,新华医院皮肤科出产一种自制的药水,效果特别好,一刷马上有用,刷几次就可以治愈了。张老师特别说,他朋友郜元宝也去刷过。马纶鹏六点才给学生上课,时间宽裕得很,听张老师这么一说,就打算下午打个车去医院看看。 张老师咳嗽,几个月了都不见好。寒假里他开车回河南老家,冷暖变化太大,不小心患了感冒。咳嗽几乎让他的写作没办法进行下去,早中晚都咳,太痛苦。他都有出全集的想法了,不再写作,把精力用来组织学术活动,就像同济人文工作坊这种。我估计这只是随便说说,他才四十岁,年龄才华都正当其时,怎么能不写? 我把上次拍的两张照片给张老师,他没有说效果本身怎么样,却认为摄影这件事本身不值得去花精力,简单地说是“玩摄影丧志”。同事坎析也是张老师的学生,比我入迷多了,几乎把摄影当作第二职业,张老师的分析一半对他一半也对我。他说,在这个年代从事摄影太容易,所以难以成功,他认为我和坎析都应该迷途知返把摄影丢开,像 小马那样老老实实去读博士。 下午我要去一家杂志编辑部开会,得早一点走。前些时候,我看到杂志招聘兼职审读人员,就投去简历,参加考试,结果通过了,这次开会就有干活之前见个面的意思。张老师问我是不是缺钱,我说不,只是随便找点事情做。他说:“不缺钱就不要去了。做个啄木鸟,多挣一两千又能怎么样?对你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有功夫不如好好看点书。”我想的是,做啄木鸟可能花不了多少时间,在这之外看书不行吗?当然,张老师的分析无疑是有深意的。既然已经到了市区,我还是去看看情况吧。将近一点钟,我告别张老师和马纶鹏,离开了同济。 和我一起到编辑部开会的总共十多人,绝大部分为五六十岁的长者。他们有的是报社专职校对,有的是杂志副主编,有的是中学校长,有的是大学教师,都出于内心的热爱来应聘这份兼职。相比之下我不仅年龄小,而且资历也浅得多。郝主编从新机构的筹备说起,介绍工作的流程,一直讲到全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文字审读领域有很多名家,像王锐祥、金文明等,在业界声誉都很高。郝主编的话让我对这片天地好奇又向往,仿佛很快就能从高手那里获得真传,自己也变得身手不凡。在一个被长者所包围的环境里,大概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吧。走出编辑部,我冷不丁想起张老师的话——我真的要做个啄木鸟吗? 假期结束之前,马纶鹏回闵行看老系主任方明光老师,当晚留了下来。我从超市买了一大包零食,马纶鹏觉得不够,一定要在校园里转转,吃大排挡,仿佛那样才更有气氛。坐在露天的座位上,马纶鹏感慨,他不认得交大了,交大也不认得他了。对于在美帝那边做学问的苦楚,他说的很少,只说那滋味亲自尝过才知道。马纶鹏硕士论文写的是1958年的中国诗歌,博士阶段 则研究1945年到1949年的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得踏踏实实。毕业后总归是进大学教书吧,至于留在美国、投奔香港还是回到上海,那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了。 马纶鹏带了五百兆空间的磁盘,用我宿舍电脑下载资料,相当一部分是电影。校园网上资源丰富,我看电影却不多。马纶鹏说,没资源的时候是一种稀缺的苦恼,资源一多就变成选择的苦恼了。我书架上有本《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是张老师在美国访学期间翻译的, 上次我在当当网定购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等一批书,顺便买了回来。马纶鹏拿起来说,他读过英文原著,非常生涩。这也难怪,就算中译本也十分难懂呢。他问啄木鸟的事怎么样。距上次开会已经一个多月,我回答说,编辑部没有消息,我也没再联系,这事估计就过去了。 正值盛夏,马纶鹏睡地铺,阳台门开着,很凉快。熄灯后我们又聊了一些,在我,这样的时光十分受用。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假,骑车驮着马纶鹏在校园里转悠。他要参观文科图书馆,要去买纪念T恤,安排多得很。我仿佛受到了他作为归来者的情绪的浸染,重新打量这片天天置身其中的校园。 马纶鹏忽然说:“日他奶奶,那不是第三食堂吗?”我说是的。当初读硕士的时候,他经常在那里吃饭。几多苦闷,几多快意,尽在这简单的问话里。下午我去上班,马纶鹏继续在我宿舍下载资料,然后独自走了。他留下纸条说,物非人非,交大就像歌里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马纶鹏很少在网上出现,不知他在那边怎么样?估计是刻苦地阅读刻苦地做研究吧。前几天我又去同济找张老师聊天,依然喝到了又浓又香的咖啡。两个人 说交大说同济说南大聊了很久,不过,再没提我去当啄木鸟的事。
2009-7-25
《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封面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张生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