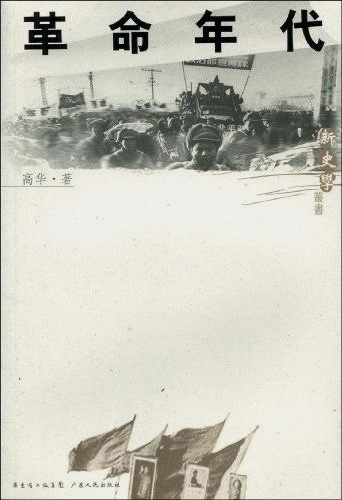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逝者,师者 ——读高华《革命年代》 ( 返回 )
遗憾的是,直到读到高华逝世的报道,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网上涌出大批文章和微博,怀念这位重新评价毛泽东、又在他诞辰日离去的历史学家。我读书工作许多年,对同一片天空下思考着的他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崇仰和谋面,很惭愧。当然最遗憾的还是,高华在57岁壮年就离开人间,带走了没完成的著作和未尽的志愿,只是留下一 尊高大的背影。越是读高华的著作及相关怀念文章,对他了解越是深入,这种遗憾也来得越是强烈。 高华的立命之作当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看到别人的推介,我马上去卓越网和当当网搜索,可惜没找到,不是卖光了,压根儿就没有这本书的上架记录。原来,《红太阳》是在香港出版的。我又到孔夫子旧书网上碰运气,结果仍然失望,连复印本也不见一点踪影。历史学界对这本著作评价非常高,“是对现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最佳解读”(熊景明《拂去历史的尘埃》),绝不可能因为“没啥看头”,不值得在大陆出版销售。实际上,国内部分图书馆藏有这本书,但是不外借,也不提供馆内阅读。一位朋友说,他在香港有熟人,以后有机会从那边带本回来看。他何曾知道,《红太阳》并不能进入内地,2003年有读者带入被海关没收,还打了一场官司。 好在,我买到了高华的《革命年代》,断断续续地读,终于在大年初一读完了。看上去是厚厚一大本,读起来却相当顺畅,一点都不觉得枯燥。最直接的感触在于,他是用心做学问的,投入感情,而不是把学术当作纯粹的外在之物。对于红军长征、延安整风,乃至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高华都有着区别于教科书的描述,不仅体现出他在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胆量,更呈示了不俗的识见和过人的悟性。不能读到《红太阳》,至少可以在这里感受他的写作风格,当作部分的弥补。读《革命年代》的时候我常想,人生在世可以感受到美食的快乐、节日的快乐、亲情的快乐,在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美好的体验,那便是思考之乐、学术之乐、阅读之乐。高华的学问有种颠覆性的力量,让读者打破头脑中来自教科书和宣传机器的现成结论,重新认识毛泽东何以为毛泽东,共和国何以为共和国,现实何以为现实,我何以为我。 《革命年代》中妙论迭出,不是著者故作高人之语,而是基于历史的事实,细密严谨地作出推理判断。对于国共两党,高华是这样看的:“20年代中国两个主要政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吸取思想和组织资源。只是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的下端结构性要素,就是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概念——阶级斗争;共产党则是将列宁主义的上、下端都吸取了,1927年之后,又融入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第136页)落笔之时,高华面对的是一种被固化乃至神化了的主流、正统描述,正像普罗大众所面对的那样;他致力于打破这种凝固的状态,祛官方意识形态之魅,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目。腐朽没落的国民党竟然也能与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平起平坐,共享列宁主义的红色资源?神圣的革命竟然可以与农民造反传统一概而论,天壤相接同日而语?高华用他冷峻而理智的笔触,把这些一一勾画出来,呈之与众。难能可贵的在于,他用有温度的思考,做出了有良知的学问。 不管是偏安香港一隅的《红太阳》,还是在大陆公开面世的《革命年代》,高华无疑都是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写出来的。中共党史有其特定的叙述模式,谁都知道,这个领域的禁忌太多了,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不好会有杀身之祸。高华让学界至为佩服赞叹的在于,从来不为申请课题、晋升职称而做学问,完全凭着一腔赤诚的热情。他要面对经济的困境,旁人的冷眼,更要克服外在环境带给他的精神压力,泰山压顶般的发自内心的恐惧感。在高华追思会上,他所在的南京大学对《红太阳》未置一词,嘉宾发言前稿件要经过党委审核,从中可见形势险峻之一斑。在书斋里面对泛黄的书卷,高华确定了自己的存在,落寞而坚定地守候着似乎被用滥了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说:“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地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回望过去。”(《后记》,第391页)高华身在书房而心系现实,将学者情怀融入著作,启发人们反思历史,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读研究生的时候,临近开题,我在几个选题间摇摆不定。导师夏中义说:做学术就像谈恋爱,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一定要充满感情,全身心地去面对。听归听,我私底下颇不以为然——恋爱这么纯洁美好的事情,做论文怎能与之相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理解了夏老师的话。在高华这里我更体会到,学问可以超脱现实利益,来得比恋爱更纯粹,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呵护。 翻阅《革命年代》,一种贯穿始终的体会是“有意思”,在捡动书页的同时,沉浸在接受新事物、产生新发现的愉悦中。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是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因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高华认为,1934年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第355页)这样的论断,读来真有石破天惊、耳目一新之感。又如,长征不仅是走出来的,也是宣传、塑造出来的。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国民党把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以前我也看到过“万里逃窜到陕北”的说法,既不高尚也不光彩;而如今,长征已经熔铸为一种光辉精神了,大张旗鼓讴之赞之。张闻天本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张闻天却不见了踪影。(《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第147页)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如万花筒般,稍微转动一下就呈现不同的模样。如果将镜头拉回眼前,一以观之,也就不难理解四处飘漾的“紧密团结在”、“深入贯彻落实”意味着什么了。 高华的文字功夫十分了得,他能够穿透表面的现象,寻幽探微,发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深层规律。毛泽东一首诗《有所思》,短短56字,在他眼中,不是诗人在随意抒发风花雪月的闲情,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领袖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有着以诗证史的意义。(《读〈七律·有所思〉》,第279页)从15本看似散乱的普通人回忆录中,高华还原出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宏大社会面貌,其归纳之精妙、论述之精当令人拍案叫绝。且看几处分析:新国家以不间断的“运动”作为统合社会的最重要方法;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具有鲜明的清算性质;工人收入和政治忠诚度存在密切关系,如此等等。(《小人物,大历史》,第303、306、320页)面对那些传记,普通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残酷、世道的艰险、人心的复杂,而得出清新简约又让人信服的结论,则非具备史家的聪慧悟性不可。高华做到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朱学勤在高华追思会上讲的一个故事。杨尚昆的儿子在读了高华写的《初读〈杨尚昆日记〉》后,到南京去找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我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人?高华回答: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这篇文章也收录在《革命年代》中。高华学问做得扎实,史料在胸,能从“无”中看到“有”,朱学勤认为这是一种可贵的洞察力。例如1965年10月19日,杨尚昆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当天日记中只有寥寥几行字,长达三小时的会谈并无涉及。但高华通过其他材料佐证了,日记中不写并不代表不重要、没动感情,事实在于,“(杨与彭)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初读〈杨尚昆日记〉》,第274页)从这里可以发现,高华读杨尚昆日记,并不是简单地从中选取某些材料为我所用,而是带着感情去体察研究对象的心境,复现彼时彼地的历史场景,作出有热度的学术判断。难怪杨尚昆的儿子对他那么佩服,专程探访拜谒。 元旦前夜,我给刘佳林老师写邮件,送去新年的问候。几小时后,他就从美国发来了跨年的回复,那时,高华的追思会刚结束两天,刘老师的心正被他占据着。信中写道: 少校,你好! 坦率地说,看到你的邮件我有一点战栗感,因为我就在几分钟之前脑子里正想着你。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我在想着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老师如何看待己出与非己出的学生,学生如何看待导师和私淑的老师。然后我就想到了你,想到应该送你一套“美国时期”,但我现在正在美国。 所以产生这些想法,都因为在看关于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老师逝世的报道。高老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国内是禁书,但在追求真相与真理的知识分子中评价极高,南大中文系董建(健)老师的挽联曰“射日成高手,启蒙著华章”,我看后肃然起敬,随即给他的儿子董晓写信,表示了我的敬意。我将这些我从未听过课的老师视为我的导师和楷模。 说远了,也说偏了。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你当做朋友的,因为老师一词,似乎于我还很远。 新年快乐! 刘老师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似乎和高华相距咫尺,很有条件相近相亲,惜乎没有听过他的课。这封邮件是一份珍贵的新年礼物。我决定顺着刘老师的指引,尽可能多地阅读高华的作品,走近这位他所敬重的导师和楷模。网上流传着高华讲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视频,十分带劲,我由此感受到了高华的音容笑貌。朋友还把其文字版打印出来。我还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董健教授撰写的“射日成高手,启蒙著华章”,回味再三,叹其贴切传神。“日”自然指那颗“红太阳”了,以高华比后羿,射日之举蕴涵着无穷的勇与谋,何尝不是夸赞他拯救斯民于灾难的壮举!我还读到了他的文章《怀念高华》,微博上很多人推荐,情浓意切,极为感人。然后就是买来《革命年代》,不紧不慢地品味,由腊月到正月,穿过农历新年,在春节的欢庆外收获了一种别样的感动。读得越多,对高华的感佩便越深,敬仰他的担当和超越,或许跟刘老师一样,心中滋长着欲拜之为师而不能的遗憾。 诚然,我也无比期待阅读高华的呕心之作《红太阳》。待时局变得清明,读到在大陆公开发行的版本,那是最好,如果条件不允许,盗版或复印本也行。但迟早一定要读。 高华不朽!
2012-2-2
《革命年代》书影。高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