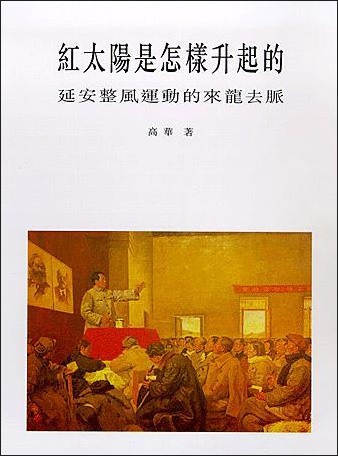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二月札记 ——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 返回 )
偶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喜出望外。从2月初到2月末,伴我早春时节。几回倚床而读,不觉夜深;几回在地铁读,长途变短途。煌煌572页巨著,却不嫌长,读来津津有味;一书之力胜过十年说教,实为激荡心魄之作。时而悲愤难耐,时而意畅气舒。对作者高华深为佩服,无限敬仰。其间记札记四则,聊表心曲。
革命是残酷的
“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 年镇压‘AB团’的行动。”(P16) 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革命竟是那样的残酷。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你死我活,誓不两立。谁打谁?两边对垒的主体,都是农民兄弟。且不说对付敌人,就看同一个革命阵营中 ,远非“春天般的温暖”。 我的脑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你是不是‘AB团’分子?说!” “我以共产党员的至诚信仰做保证,我不是。” “怎样证明你的信仰?”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的神圣事业。” “党需要你为革命需要承认你是‘AB团’分子。” “我不是!” “你不承认,就是反对党的事业,投机革命。必是‘AB团’分子!” “……”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革命理想的名义,个人的生命瞬间化为虚无。 还有另外一种画面—— “你是不是‘AB团’分子?说!” “我不是。” 竹签从指甲缝穿进肉里,香火慢慢在身上烧,手指被折断。撕心裂肺的哭喊从审讯室传出。 “你是不是‘AB团’分子?” 一个气息微弱的声音回答:“是。” “张三是不是‘AB团’分子?” “也是。” “终于承认了,拉出去枪毙。把张三抓起来审问!” 红色恐怖在苏区蔓延,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革命是一台冷酷无情的机器,不仅消灭了敌人,也绞杀了自己人。而当它一旦运转起来,便具备了惯性,源源不断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软硬兼施,穷追细问,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这不是小说中疯狂的国民党反动派折磨地下党的手段吗?不,是发生在共产党的阵营里,“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P42)数以千计的革命者,含冤死在了同志的屠刀下。何异人间地狱,革命是残酷的! 萧克将军在1982 年曾回忆1930年12月的一次刑讯逼供:“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P26) 为什么要肃反“AB团”?革命需要。既是事实,也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史料已经证明了,内中不乏剪除异己、扩充个人实力的动机。把嘈杂的声音归为一种,轻声细语的说服、风和日丽的讨论是无法做到的,必须让挑战领导者权威的人付出代价。于是,悲剧不断上演。 “几年后,毛泽东把这股情绪导引至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俨然自己一身清白。当毛将党和军队大权牢牢掌握后,知情人纷纷三缄其口,最终,肃反问题反而成为毛泽东打击王明等的一根大棒。”(P57)脏水泼到政敌身上,真相被掩埋了,直到如今,“正史”中王明依然是替罪羊。这何尝不是革命的另一种残酷!
2012-2-6
真相凶猛
他的名字不仅写进了党章,还写进了宪法。提起他,人们会想到四个“伟大的”,想到“战无不胜”,以及更多的褒扬性描述:高度自信的沉稳和持重,坚强的意志力,当仁不让,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接人待物诚恳、得体,谦恭有礼,如此等等。这里还有一份含义完全相反的名单,不见于正史,却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接受——浓厚的“山大王”气息,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睚眦必报,猜忌防范心重,咄咄逼人,峭刻嘲讽,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金刚怒目,自大,专断,心高气傲,多疑善变…… 没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都是说的毛泽东。前者是表面上的、各种宣传舆论着力塑造的,后者是高华基于详尽的历史资料总结评判出来的。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泥像轰然倒塌,扬起浑浊的尘土,留下一片颓败的废墟。 王明从苏联归来之际,毛泽东站在各界欢迎队伍的最前列,“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而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挖苦王明(P149)。“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仪仗莫斯科地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P121)围绕权力的争斗无时不在,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打击对手。毛泽东与王明共事几年,用之忍之,终于除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写亲笔信给蒋介石,赞扬“先生盛德”。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盛赞蒋介石,称国民党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与基干地位,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P150)然而就在不到一月之后,六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变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抨击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奏不斩”的灵活策略。(P153)翻手为云覆手雨。所谓诚信,所谓人格,所谓涵养,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对于习惯了撒谎为自家贴金、习惯了仰望领袖的人来说,真相来得凶猛可怕。历史学家梳理发现,《新阶段论》在收入《毛选》时被改名并大量删减(P150);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全文不曾刊登在国内任何公开出版物,可见于台湾的论文集,蒋介石日记、《周恩来年谱》中也有佐证(P151)。随着真相的大量呈现,真理也就水落石出了。 近一个多月来,我时常默念南京大学董健教授悼念高华的挽联“射日成高手,启蒙著华章”,越来越敬服这位射日高手的胆量与能耐,最近才突然领悟到,挽联中镶嵌着高华的名字。在海量历史文献中披沙拣金,如蜂酿蜜,如蚕吐丝,将最宝贵的成果献给世人。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这是一本推倒偶像、终结神话的大书,一部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终将影响历史进程的厚重著作。
2012-2-8
历史即政治
初中时要上很多门课程,历史和政治都在其中,有个事实心里很明白:历史是历史,政治是政治,两者教材不同,授课考试不同,考卷也不同。在读《红太阳》的时候,我却越来越相信这样的判断:历史即政治,对历史的撰写与解释,正是权力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外现成的例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P161)该书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为了维护其一贯正确的形象,不惜任意裁剪历史。(P162)这部党史成了斯大林美化自身形象、巩固手中权力的工具,不能不说是直截了当的政治。 很多人都熟悉“马恩列斯毛”的说法,五张画像一字排开。斯大林这个以铁腕手段对党内同志搞大清洗的刽子手在中国高居神坛,与毛泽东对他和《联共党史》的推崇密不可分。毛泽东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解释课本,对斯大林编的这部党史吃得最透。他在干部会上极力推荐,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列为整风文献,后收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年至1956年,《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科目,直到60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泽东选集》所取代。(P160)。《联共党史》纳入了官方认可的知识体系,哪怕是异国读者,也自然对斯大林敬仰有加了。 毛泽东不仅喜欢《联共党史》,而且得到了其中的真传,哪怕极为肮脏龌龊。1940年,羽翼渐丰的他想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否定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却受到了张闻天等党内大老的抵拒。在这种情况下,他主持编写了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以党内所谓“两条路线”为经纬编排史料,将自己树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毛泽东为了表明一贯正确,对有碍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删除,甚至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做手脚。《六大以来》的杀伤力是巨大的,给党的核心层带来猛烈的精神冲击,只得向毛泽东俯首输诚。毛泽东自己都说,“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P173-176) 历史可产生“解除武装”之威力,堪比军事上的机枪大炮,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利用历史。1943年至1945年,他亲自主持,编写了以他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本《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里面只有他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活脱脱一部中国版的《联共党史》。(P162)以后的事情更说不过来了,这运动那斗争的,别人都是错的,他是不倒翁。有句话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不是吗?如今,毛泽东的头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被很多人当作“人民的大救星”。 孙悟空抡起金箍棒向白骨精一阵猛打,妖精就现了原型。高华的《红太阳》正是一部蕴涵着非凡力量的历史著作,揭去虚掩的面纱,显出历史的真容。《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他的野心,也犯过很多错误。当前,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依然敬奉毛泽东,将他的名字写入党章,自然难以容忍诋毁偶像的文字大行其道。《红太阳》在内地不能公开出版,岂非“历史即政治”的别样例证?
2012-2-9
自我照亮
说起填写个人情况表,你一定会觉得熟悉,从上学到工作,不知要填写多少张。看到“家庭成分”这一栏,糊里糊涂,心想填了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意思。升入初中以后,我对填档案印象格外深刻,班主任在讲台上再三叮嘱:必须他说一个空就填一个空,绝对不能私自往下填,错了一个字,整张表就得报废。写字不好的同学还得委托写字好的人填。有点门子的人为了初三复读,提早做两套档案,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多上一年然后考高中了。个人档案是很神秘的东西,自己根本看不到。读研之前,我去黄浦 区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办理迁户口手续,看到自己的档案被工作人员拿着,只有几米之遥,但是不能看到内容。后来,档案怎么流转,存放在哪里,就全然不知了,说来并不能称为“自己的”档案。 如果要问填个人档案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可能就回答不出来了,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起源于哪里,不需要问为什么。“上级”需要,“组织”需要,不就够了吗?前面若干年,我也这么认为,从没去考虑这些表格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历史,怎么样的权力关系。直到高华的《红太阳》告诉我,这样的传统兴起于延安整风时期。要填写“小广播表”,要写自传,写一遍不过关要写好几遍。 轰轰烈烈地“审干”,各色人等被“抢救”,被“肃反”,或者被剥去一层皮,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或者成为革命的对立面,被关押改造,乃至杀头枪毙。高华写道:“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的一件利器,它同时成了一只‘不死鸟’。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完全是独立于干部个人的异物。”(P374)相比于那个年代,现在填表格似乎宽松够仁慈得多,但谁知道呢?仿佛一个人造的魔鬼,暂时装在瓶子里,得着机会就出来捣乱为害。 这是一本厚厚的书,大大的书,它蕴藏的思想资源多之又多,拿起来随便翻看几页,马上进入到吊诡而荒谬的历史中去。在通常的表述中,那段岁月是充满光亮的,积极友好的,团结向上的。通行的历史来自于胜利者的书写,但真相不会被长久地掩埋,总有重见天日的时候。高华进行了规模极为浩大的梳理工作,把散落在公开文件、领导人文集、私人回忆录中的相关材料归拢起来,凝成一个水泥墩子般坚固的整体,他作为史家的非凡识见则是坚韧强壮的钢筋。“文革”的发动抛开了党的 常规机构,临时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权力机关,只对一人负责,原来这是很后边的事情。政治局被冻结,中央总学委领导整风运动,已经是大获“成功”的演绎。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以及对领袖的不遗余力的颂扬,都能在延安找到渊源。可以说,延安远非罗曼蒂克的桃花源,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城堡,它预示了1949年以后中国的革命化图景。 老干部老功臣被打倒了,痛心;同一个阵营里的人相互揭发打击,痛心;人失去了自由向善的天性,变得不像人,痛心!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说:“尽管毛泽东肃反手法多变,与一味屠杀党内同志的斯大林有明显区别,但两人在利用肃反消灭政敌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P386) 还有,“作为极左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运用这一套手法对付他的假想敌人时已达到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地步。”(P388)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也是一样吗?他曾经的亲密战友们,刘少奇、彭德怀、康生、张闻天,乃至党外的章伯钧、储安平,谁得安生?他哪里是什么“大救星”?!分明是 一个恶魔,甚至够不上倒三七开。高华诚然射日高手,《红太阳》也像一面照妖镜,映出“一代伟人”的真面目。他原本如此,高华所做的,不过是排除干扰,说了真话。 一般而言,“整风”是个中性的乃至带着几分褒义的词,作为一场运动,它残酷无情的那一面却被遮蔽了。“逼供信”害死了多少人!整风实际是整人,来个有罪推定:出身地主、资本家的,来自国统区的,坐过国民党监狱的,都有问题;有知识有文化更是一种罪恶,必须放下身段,向没留过洋的最高领袖屈服。这种“知识反动”的逻辑弥漫开来,将五四以来的自由民主风气拦腰斩断。不能说毛泽东是土包子,因为他毕竟度过很多书,也很有文采,但他实际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反右”中多少知识分子遭殃,“文革”中成了“臭老九”,一切都不是凭空而来。 启蒙这个词,我经常听到,记得初中历史中有关于启蒙运动的章节,但具体什么意思,并没有多想。下意识好像觉得,是在一个阴暗消沉的时代,有高人傲然站出来,振臂一呼,带领普罗大众去除蒙昧。现在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就个体来说,对于某段历史、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判断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加,比如教科书的灌输,毒辣的红太阳的照耀,而是来自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自己带领自己走出黑暗的境地。简而言之,启蒙就是自我照亮。高华从来没有故作姿态,只是做他的研究,重写历史,但由于他的非凡的史识、勇气和辛劳,他的书实际起到了启蒙教材的作用。 真遗憾,高华已经走了,他再也不会知道读者的体会。但《红太阳》是一本不死的书。读着它,我仿佛看见高华沉静思考、秉笔直书的情景,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高贵与纯粹。我紧紧握着书,使劲摇一摇,当是握着高华的手,向他致敬。
2012-2-29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影。高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