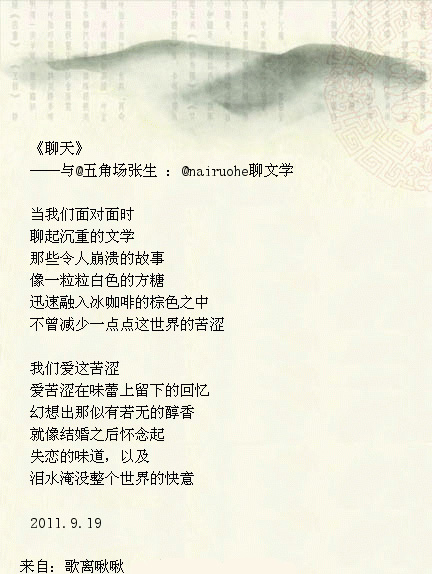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都市唱游 ——读李刚的诗 ( 返回 )
2002年春天,莫言和王安忆在上海图书馆作了一个讲座,主题叫“写作,是悲壮的抵抗”。读到李刚的诗,我不由就想起了这句话。远的不说,在最近的四个月里,李刚总共写了80首诗,每一两天就有新的作品。他有正式工作,要给领导草拟讲话稿,制作公司庆典的策划方案,只是放不下诗。写诗成了他生活的常态,也是抵抗虚空侵扰、通往理想之国的途径。 人在城市,少不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不管身在哪家单位,总逃不开弥漫在职场江湖的爱恨情仇。毕业后的十年间,李刚换了约摸十家公司,他常常以旁观者的自居,和周围习惯于谄媚、告密、推责、争功的人们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性格障碍者\常常被自己的脚跟绊倒\常常坐在角落里\像一只懒散的灰猫\神情淡漠,对他们的欢欣鼓舞\扭过头去,打起了盹”。一方面,作者没有回避“我”在“他们”眼里的病态形象,似乎很可悲地没能融入主流的世界,但“我”又是清醒的,自知的。在诗的最后,作者骄傲地宣布“是的,我确实视他们不见”。很显然,这首《在他们眼里》中的“我”可以当作李刚的自况,也可以看成他着意塑造并非常推崇的一类人,在混浊的环境中卓然独立。 每日一诗或者两日一诗,思考的脚步从未停歇,李刚顽强地进行着一场文学的马拉松。在纷纷攘攘的都市,不合时宜地唱着田园牧歌。在一个资讯密集、口水式表达盛行的年代,他完全是一个异类。这也就不奇怪,周围的喝彩很少,发表在博客上的诗,单篇阅读量 往往为个位数。但李刚又爱上这差事了,他说,不写点什么,就觉得日子过得空,不踏实。 借助诗歌的形式,李刚留下了他对生活的感悟与观察。他有一双灵慧的眼。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普通的场景,以敬重生命的名义,在文字间凝固下来。他很少热情地讴歌什么,也很少激烈地诅咒什么,外在的世界经过了他的打量,变得宁静平和。比如《雨》,“仿若神的孩子,尽情地跳着\转瞬即被吸入水面”,活龙活现。这种宁静和平和中,分明带有某种嵌入了时代内核的东西。《他们埋掉了撞毁的车头》副题“为7·23温州动车遇难同胞而作”,末节这样说:“他们埋掉了希望\但埋不掉绝望\绝望生出的野草\能拱起巨石\把它抛下山崖”。读者能够看出他对现实的关注,体会到一种含而不露的愤怒。 李刚的诗平白易读,不长,没有生僻的字,很少四字成语,随便拿出一首,小学五年级的孩子都可以读下去。当然,用字深浅和诗味浓淡绝对是两回事,浅有浅的味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信请看《每周的最后一件事》,既短且白:“每周的最后一件事\是打电话回家\每次谈论的话题\首先是吃饭,天气\然后是母亲的健康\最后是我很好,放心吧\\每周都是如此\对于母亲的牙痛、失眠和白发\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这是很多人熟悉的场景,两代人有规律地打电话,说吃饭、说天气,报喜不报忧。他捕捉到这样的片断,用有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便成了诗,好诗。 面对诗歌,李刚是真诚的,甚至可以说奉若神明。前几天,我和他一起去看张生老师。聊起写作,张生对这首打电话回家的诗印象深刻,很是喜欢。李刚疑惑,他写诗常常觉得在某扇门外面徘徊,没有登堂入室,随便拿别人的诗集看,都觉得自己写得太差了。张生很不同意这样的比较,他说:“你看到一册《里尔克诗选》,觉得每一首都很好,别忘了这是他几十年所有诗里面选出来的,是最好的部分,你当然没法和他比。写作是个技术活儿,坚持写下去,到时候你精选一册,肯定也非常漂亮。” 现在很少有人听过歌义松、歌离啾啾的名字,这正是李刚的笔名。以他的才情和勤奋,出版诗选当指日可待。相信有那么一天,人们会更多地认识他,暗夜里的清醒者,温柔乡里的长跑者,喧嚣都市的唱游者,诗人李刚。等他刚满月的孩子长大,一定会谦诚而自豪地在心里默念:“我爸是李刚。”不因为他的权势多么显赫、财富多么傲人,只因他身上流淌出来的澎湃的文华诗才。
2011-9-19
链接:李刚的诗(新浪博客) 转载:奇点文学
李刚诗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