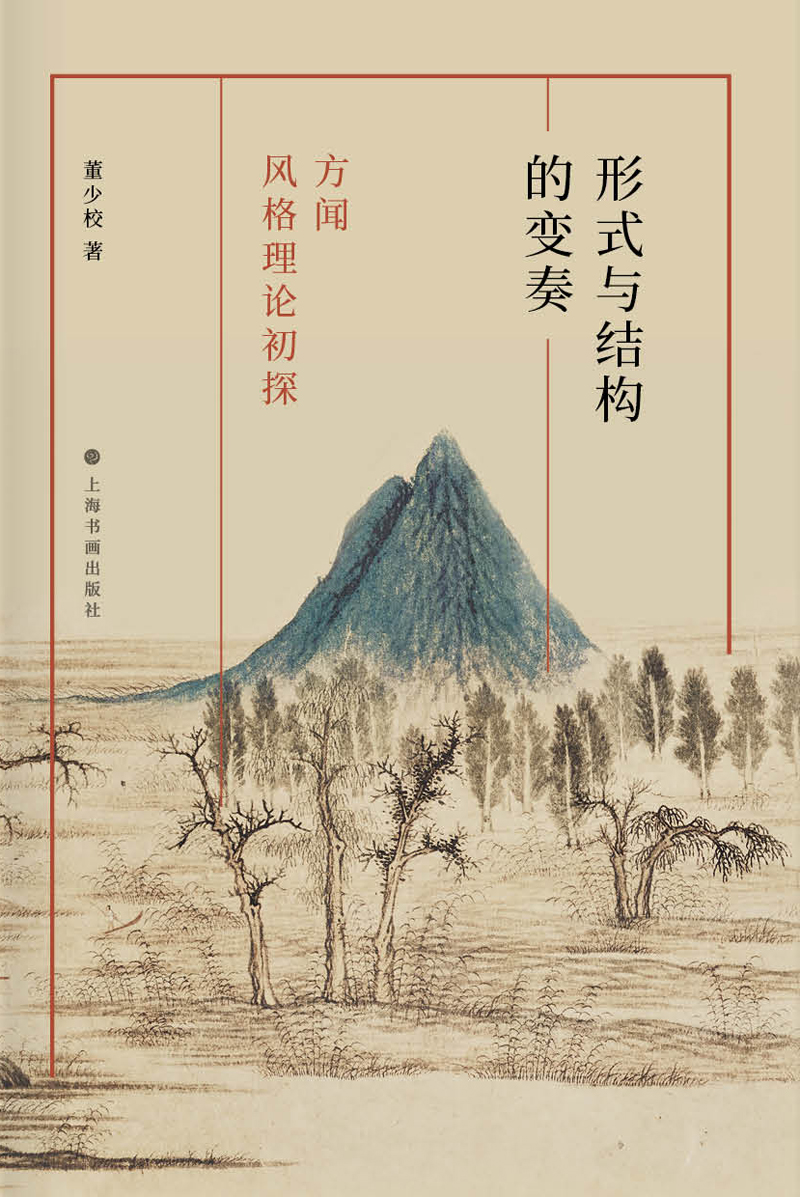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形式与结构的变奏——方闻风格理论初探》概要
( 返回
)
《形式与结构的变奏——方闻风格理论初探》,董少校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张生作序。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音乐学院资助。
内容提要
方闻(1930—2018)是一位杰出的美籍华裔艺术史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此直至退休,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研究,并推动美国两所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他借鉴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将形式结构分析引入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取得卓著成果,形成富有阐释力的风格理论。
本书聚焦方闻艺术史研究,围绕其关于绘画与书法风格、书画同体、再现与表现等关键论述,对其以风格分析为主线的艺术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通过绘画风格与书法风格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风格分析法与非风格分析法相结合,多角度解析呈现方闻的风格理论。
方闻建立了一套宏大完善的风格理论体系,对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提升中国书画国际地位作出重要贡献,在中西艺术文化交流中架起一座天桥。
链接:上海书画出版社7月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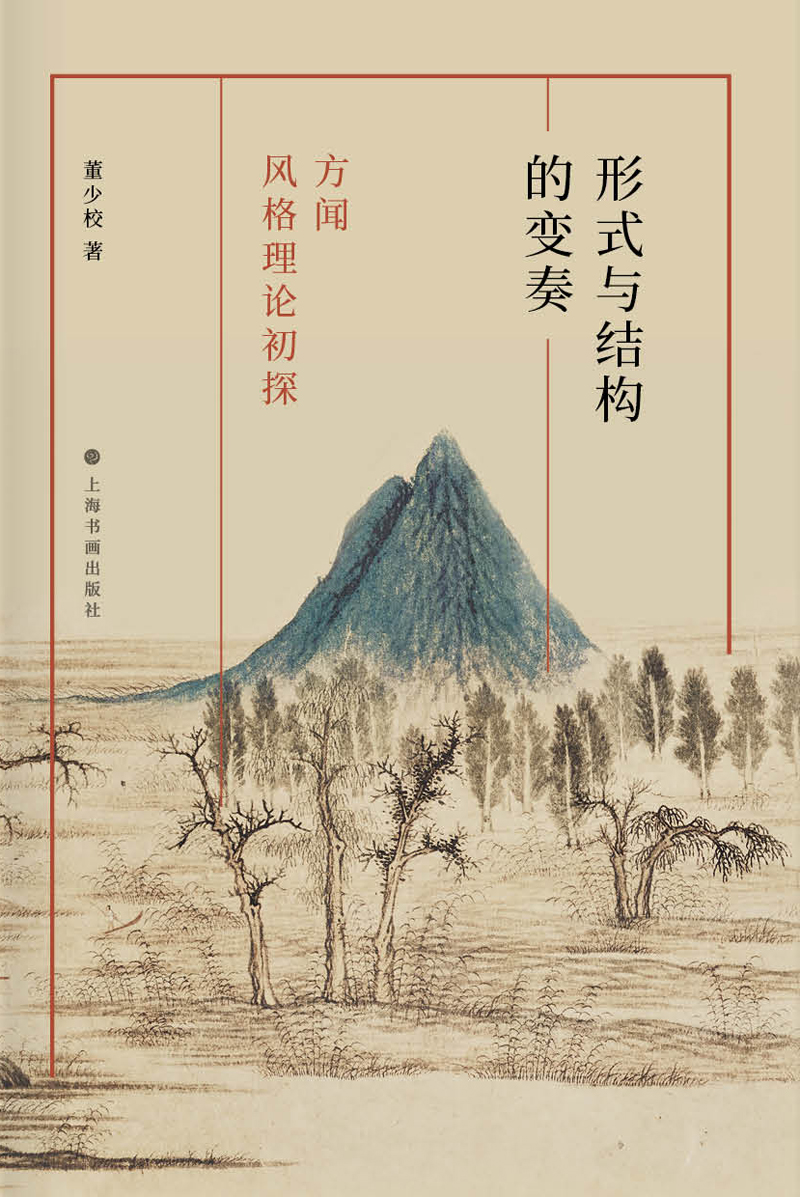
序言
董少校的博士论文《形式与结构的变奏——方闻风格理论研究》经修订后即将出版,我们有多年师生之谊,他几次请我写几句话以为序言,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很少为人作序,也不喜欢别人为我的书作序。我觉得,一个人的著作总有其自身的价值,既不会因有谁的序而增色,也不会因缺少了谁的序而减少其光芒。而少校的这部研究方闻先生美术思想的专著,就是一本有着自身特色及独到价值的著作,我认为并不需要我画蛇添足予以推介。但在他的坚持之下,作为他在同济大学攻读美学博士时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我也只好勉力谈谈与他的这篇论文相关的一些东西。
也许,首先可以谈的就是少校何以选方闻先生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与我的建议有一定关系。方闻的名字,我是2006年春天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时无意中得知的。那天,当我顺着博物馆的参观路线来到了二楼时,忽然看见一座粉墙黛瓦的中国庭院,这让我在倍感惊讶的同时也觉得无比亲切。我漫步在这座英文名为“阿斯特庭院”(The
Astor
Court)、中文名为“明轩”的中式古典建筑里,看着里面陈设的散发着古雅之美的暗红色的明式家具,庭院里的灰白色的太湖石和绿色的芭蕉叶,觉得像突然走进梦中一样难以置信。所以,当天我回到住的地方后,就立即上网查了这座中式庭院的来历,才知道它是苏州网师园中“殿春簃”的复制品,而主持其事的就是时任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的方闻。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我还从网上很意外地发现方闻这个普林斯顿的艺术史博士竟然在1948年出国留学前就读于交大物理系,而参观时我正任教于交大人文学院,因此平添了一份亲近之感。当时我就想,以后有机会或许可以写点关于方先生的文章,可第二年回国后不久我就调到同济工作,这个念头也就不了了之了。
又过了几年,少校联系我来同济攻读美学专业的博士,在他与我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的这个念头重又萌发出来。少校本科就读于交大能源工程系,后来又考回交大人文学院攻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我曾教过他文艺学方面的课程,对他的兴趣很了解,他喜欢篆刻和书法,业余时间不仅自己治印,还写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我觉得他的经历和同为交大校友的方闻有共通之处,都是由理工而入文艺,也许在研究方闻时会比他人多一分“了解之同情”而别有会心,所以我就推荐了方闻供他斟酌。他很慎重,在阅读方闻的相关资料后又和我反复讨论了几次,最终才确定以方闻的风格理论为研究主题。这大概就是少校这本著作的缘起。
其次,可以谈谈方闻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意义。宗白华先生曾言,中国的绘画,与希腊的雕塑,德国的音乐,可“鼎足而三”并立无愧色。因此,中国绘画也足为“世界文化史”高峰之一。他以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等德国思想家的眼睛审视中国古老的艺术,观人所未能观,言人所不能言,让中国的书画在千百年后焕发出别样的光辉。他谈中国艺术的意境,谈绘画的生动的气韵,谈书法的音乐的律动,都是为了激活其古老的生命,返本开新,重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因此宗白华借助德国哲学家的思想批评中国美术时,有取精用弘、超以象外之感,而方闻借助潘诺夫斯基、沃尔夫林、贡布里希等德语艺术史家的方法,切入中国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之中,却如庖丁解牛,细致入微,以求阐明中国绘画及书法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中所具之独一无二的价值。
与宗白华致力于用汉语写作、向自家人开掘其美学精神不同,方闻有关中国美术的著作侧重于向域外尤其是北美艺术界介绍其美在何处,大多用英文写成。这也使得他的著作有种“陌生化”效果,既可以如宗白华所言借“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面孔”,也可以让人知道“外人”对中国艺术的观察的视角与方法。也许,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艺术的伟大之处,因为我们距离那些大师们的绘画可能并不比外人更近。相较而言,对于中国绘画的观看与阅读,方闻所介绍和提倡的“风格分析”,或许更符合现代人的“法眼”,以让我们今天早已习惯了“看”画的眼睛,可以重新像之前的人那样“读”懂其中的奥妙。此外,方闻研究视野的开阔,使得他可以从容地把中国的绘画艺术放在世界艺术发展的范围内进行考察,或如尼采所言的那样“重新估定其价值”,给予中国美术以真实的评判,既不盲目自夸,也不盲目自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获致真切的“艺术自信”。
再就是可以简单谈谈少校的这部博士论文。少校从形式与结构这两个关键概念入手,对方闻的风格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并以此为据,对其风格理论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其在中国艺术批评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批评,可谓切中肯綮。应该说全书观点清晰,论述得体,且要言不繁,是目前较为系统的研究方闻美术批评思想的专著。但可能正是因为这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研究方闻美术思想的著作,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对方闻的美术批评思想介绍居多,对其理论生成及展开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另外未能将方闻的风格理论放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如将其理论习得置于北美乃至世界艺术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予以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所以略显单薄,此外对方闻具体的美术活动的研究也涉猎较少。当然,因为方闻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且其主要的批评场域又在海外,要真切地还原其语境并完全把握其丰富的指涉有相当的难度。这些不足,或许也是少校进一步研究的动力和方向。
最后,对上海书画出版社对少校这个青年艺术学人的扶持也应表示感谢。书画社曾出版了很多方闻著作,我记得方闻在大陆的第一本专著——李维琨先生翻译的《心印》就是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少校的这部著作能够在书画社出版,对其方闻研究及将来继续从事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是一种有力的鼓励。
勉力为少校的著作写下这个不知道是否可以算作序的序后,我颇有言不及义之感,所以,我很希望以后这本著作再版时,少校可以去掉这个序。
张生
2021年5月7日于同济三好坞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21年7月22日“法国理论”微信号刊登此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