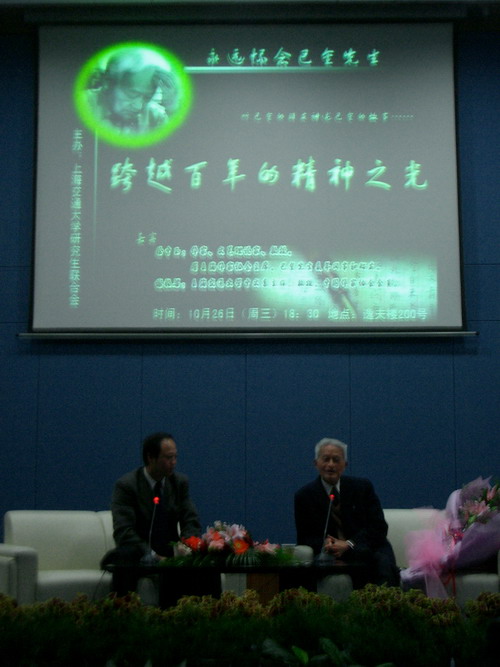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跨越百年的精神之光 ——交大学子聆听演讲缅怀巴金老人
10月26日,上海交大研究生联合会邀请徐中玉教授到闵行校区举办报告会,追忆伟人风范,传承巴金精神。徐教授回想了和巴金老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巴老“讲真话”精神的崇高敬意,并对《随想录》的思想意义作出了精辟的解读。本次活动由中文系主任谢柏梁主持,数百名交大学子聆听了徐教授的精采演讲。
他是中国文艺界的良心
徐中玉教授认识巴金老人是1947年到上海以后的事情,在那之前他已经阅读了《家》《春》《秋》等作品,并从中受到了很多影响。1989年,徐教授当选上海作协主席,而巴金老人是上海作协名誉主席,他们有过很多接触的机会。两天前,徐教授刚去殡仪馆参加了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他的印象里,巴老是个和善而诚恳的人,做事认真,文章不写一句空。十年“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很多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后来他勇敢地拿起笔,把自身的曲折经历写了出来。徐教授说,巴老在“文革”中吃过很多苦头,可他回顾历史并不是为自己申冤呐喊,而是在深刻地剖析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很多人对“文革”抱着一种马马虎虎、不闻不问的态度,巴老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拖着老病的身躯,写下了一篇篇内涵丰富、情感真挚的文章。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对国家怀着无比的忠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在人人想说而不敢说的时候,巴老作为先行者挥起了“讲真话”的大旗。徐教授觉得,巴老是中国文艺界的良心,也代表了中国文艺界的灵魂和良知。他主编过多种版本的《大学语文》,每种版本都会收入巴老的文章。
“文革”博物馆一定会建起来
晚年的巴老一直在呼吁两件事:一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馆。文学馆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慢慢成长起来了,而“文革”博物馆的诞生却似乎没有一点迹象。巴老在“文革”中失去了亲爱的夫人萧珊,他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无奈地离开了人世。徐中玉教授说,在巴老的心目中,十年的沉痛教训需要总结,历史的悲剧一定不能重演了;博物馆是凝固形态的历史,建立“文革”博物馆是非常有必要的。巴老的这项提议没得到多少回应,内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过徐教授说,时代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广东、四川等地已经有了民间的“文革”博物馆,将来定然会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文革”博物馆在中国建立起来。
《随想录》是一部不朽的大书
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之后,徐教授和同学们开始了互动的交流。虽然已经是九十一岁的高龄,可是徐教授思维敏捷、言语清晰,对每个问题都能做出让人满意的回答。有同学提出,大家都说《随想录》多么好多么好,它到底有怎样的文学价值呢?徐教授说,《随想录》并不是以文学技巧取胜的,它结构并不见得严谨,词句并不见得精美;不过从思想上来说,它是一部大书,是不朽的。巴老亲历过“文化大革命”,他在这部书里讲了真话,非常坦诚;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场浩劫。他在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着想。巴老倡导人们独立思考,而他自己就是独立思考的典范。徐教授的回答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演讲结束时,主持人谢老师作了简单的总结。他说,在巴金老人刚刚离去的日子里,徐教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人格的塑造方面,我们不能像像商人那样急功近利、注重短期行为,而应该像巴老那样,做诚实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人。巴老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活了一百零一岁,而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赤诚之心,因为他代表了上海乃至中国学术界的良知。谢老师动情地说,交通大学已经有过上百年的时间跨越,将要迎来110岁生日;只要大家都能够从自我做起,说真话,做真人,交大的明天会更美好,中华民族的明天也会更美好。
2005.10.26
(刊于2005年10月31日《上海交大报》,刊登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