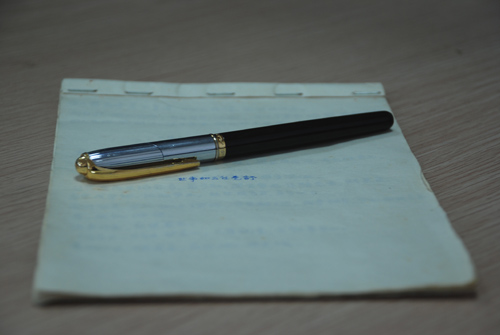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余下的全归你 ( 返回 ) 演讲厅门口摆着贾樟柯的书在卖,一本《贾想》,一本《中国工人访谈录》。我进去找个位子,把包放下。屈老师告诉我,贾樟柯已经在贵宾室接受记者采访,叫我赶紧过去。媒体不多,我在旁边听着,给他拍照片。那年轻女记者问:你的电影为什么不关注都市题材?贾樟柯说,《二十四城记》就是都市题材。她补充说:我是说一线城市。贾樟柯轻松地回应:《世界》发生在北京呀,那不是一线城市。感觉这记者真是太搓了。 我得了空把《上海交大报》关于贾樟柯的报道给他,又问,电影中关于爱情的分合是本着怎样的原则去处理的。贾樟柯说:爱情跟自我有关系,里面包含着自我的意识,《三峡好人》里面,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都是强大的自我在发生作用。《任逍遥》中巧巧在挣扎,因为有束缚所以希望挣脱,有了任逍遥的要求。主办方搬过来一大摞书,叫贾樟柯签名,不知是准备送人还是售卖。这样他就有点心不在焉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直到演讲开始,听众还是稀稀落落,没坐满,人气比《三峡好人》首映式那次差远了。我给嘉硕发消息说,我在前排正中间,留了位子。他很快就回复我了,说是坐在后边。我回头一看,可不是,几乎在最后边了。贾樟柯演讲的主题是“聆听沉默工人的记忆”。因为一个小小的机缘,他听说了成都420工厂的故事,进入,采访,梳理,重新创作,两部作品就出来了,一是电影《二十四城记》,二是书《中国工人访谈录》。以前我关注的是贾樟柯的艺术才华,这次更认同他的创作姿态:到一个地方去体验,挖掘,倾听一个群体的声音,通过某特定地方的变迁,折射出整个时代的跃动轨迹。简单地说,他是真诚的。就冲这一点,我还是买了一册《中国工人访谈录》,排了队找贾樟柯签名。 嘉硕很不满意的是,互动环节只是泛泛而谈。有MBA模样的提问者夹着英文单词说半天,实际什么也没说,根本不需要主讲人作出回应。嘉硕做着与影视圈比较接近的工作,编剧。下了班后他直接赶过来,没吃晚饭,我也没吃。等我买了一册《中国工人访谈录》并排着队叫贾樟柯签好名,两个人一起去找饭馆。走在新华路上,周围黑魆魆的,说话的时候不用看着彼此。嘉硕借用网上的话说,《二十四城记》是伪纪录片,如果拿到国外去,谁也分不出哪是真工人哪是假工人。演讲中贾樟柯说,他期望加一些大家熟悉的演员,让观众知道那不是纪录片。嘉硕不看好贾樟柯,认为他成不了大师,《二十四城记》已经呈现疲态了。我看不到那么远,比较新的导演,要数十个数五个,总包含贾樟柯吧?他还不到四十岁,艺术创作正渐入佳境呢,何况原本就有文学的底子。 番禺路上的重庆鸡公煲,这个我喜欢。学校里也有一家,每次去吃都觉得大饱口福,那就再享受一回吧。表哥以前说,对鸡公煲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有一起吃过。人不多,我和嘉硕坐到最里面的位置,点菜。每次我都会点鸡鸭血、粉丝、豆腐、花生,别的就无所谓了,随他。然后两瓶啤酒。不远处有一男一女两位韩国人,我不时的瞟一眼,女孩子后背对着我。 找工作太不容易,嘉硕对这感触太深刻了。从深圳回来后,他费了不少劲,才找到现在的位子。四五个人的小公司,老板和他差不多大,其余的都是85年或者以后出生的,包括老板娘在内。老板自己当导演,嘉硕写剧本,拍摄场地、设备等都是租的,演员也临时拉。小公司没什么竞争力,只能靠压价,一条广告10万块,没多少赚头;大公司则可能要价150万。差别就这么大。嘉硕说,这个行业和电影的区别在于,它是不加遮掩的商业行为,目的是让观众看过广告之后马上掏钱买,立竿见影;电影则含蓄得多,要艺术化地讲一个故事。上海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有成百上千家,但是做电视购物编剧的则少之又少。小公司不可能花半年时间去培养你,今天过来,明天就干活,不玩虚的。生手来了,谁知道你几个月后还在不在这里。小公司的老板也痛苦,过来应聘的人多的是,一看简历,以前没做过这行,免谈。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也不容易。嘉硕说,大环境就是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哪怕老板的导演水平一般、公司小不那么稳定,也无所谓了,先干着。 我胃口很小,吃一点东西就饱了。高中的时候还是很能吃的,一天三餐吃馒头,四两六两四两,一点点菜就可以把饭带下去。火锅是慢悠悠地吃,菠菜粉丝随便挑,肉饺就吃不动了。第二天早上我在管院有另一个采访,跟嘉硕说好了,在他那边住一宿。反正时间宽裕,可以从容地吃,尽情地聊。 说到贾樟柯的时候,我问嘉硕有没有看些类似风格的文艺片。他说,不看,下班之后就很累了,有那两个小时,情愿找部大片,放松一下。在这种忙碌的状态里,写点东西也变得奢侈了。我不由自主就想到他写的《藏玉佛》,故事扣人心弦,文字也富有民族风情。如果不写一点,岂不是浪费了才华。嘉硕说天天想的是弄广告那一套,脑子僵化了,要找个时间调整一下。 忍不住我还是会问:你咋还不着急呢。嘉硕胡茬很长,是带着几分苍老的那种成熟,实际他比我还小一岁。不急,一贯不急。怎么说他也是靠近娱乐圈的人,别说是绯闻了,蛛丝马迹都没有。他闲时主要是玩游戏,看片子。说到了我分手的事,他说,哦,这个太常见了。他室友秦木一年里经历过的分手不知有七回八回。在深圳那阵,中午他和女朋友要出门,神色凝重地对嘉硕说:“我们分手了,我去机场送她。”晚上,两个人一起回来,秦木笑嘻嘻地说:“我们回来了。”仿佛压跟没有分手这回事。嘉硕不急,是想再等几年,基础厚实一点,有选择的余地。现在什么都没有,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对付。如果一个女孩子认同他的处境,愿意和他一起过,那也可以;可是没有。家人呢?他们当然希望早一点,快一点,不过上海的艰难他们也知道,提供不了实质性的帮助,没法催促。这个思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嘉硕说出来了,也很能够理解。 吃完火锅已十点多了,我们往回走。嘉硕的住处在广元西路,离学校很近。这里正在动迁,搬走一户就砸一户,所以小区里显得很破败。嘉硕指着一条横幅对我说:“你看看他们,一面说‘早搬迁早得益’,一面说‘舍小家为大家’。前面是用经济利益来刺激你,后面给你戴上道德的高帽子;前面意思是,搬迁是件好事情,不搬就亏了;后面意思是,搬迁会让你牺牲一些。显得很糊涂。”那横幅已被风吹卷了一角,不过还是能看出原本的样子:“早搬迁早得益 早搬迁早安居 舍小家为大家 顾大局为国家!” 这房子我很熟悉。我第一次住下来,是在2007年。那时候我在静安区经委实习,九月初九重阳节,单位里发了十只大闸蟹,我一个人吃不了,来找嘉硕一起吃。碗筷盆瓶乱糟糟的,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螃蟹体形很大,分成两次才煮完。记得那次喝了黄酒。秦木要很晚才回来,两个人又吃不掉,我发消息叫表哥一起来吃。结果是不肯来,本来我想介绍给嘉硕认识的。什么逻辑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当时是叫了。我和嘉硕一共吃掉七只,剩下的放冰箱里给秦木留着。我喝黄酒很上头,走不动了;同住的海山那几天在外面拍电影,我就睡他床上。第二天是周六,睡迟了也不要紧。 房子要动迁了,嘉硕在里面就有住一天是一天的意思,等别人搬得差不多了再换地方,反正房东不催,房钱也好商量。以前有室友已经搬出去了,所以有空床位,还是原先海山的那个床,上面空荡荡的,嘉硕找了两条被子出来,不知是秦木的还是谁的。两个人看了一阵子电视,随便聊聊,到了十二点,我再也支撑不住,回房间去睡。 哪怕关了窗子,外面空调滴水的声音还是历历可闻。看电视的时候困得不行,这时候反而清醒了,不由得想起了表哥的事,好像与这幢房子有关。年前,我曾经从这里出去,到港汇下边肯德基去见面,带回一件毛衣。后来不开心了,拉倒,不过毛衣还是穿了一冬。生活变化了很多,又好像没有变化,一天一天,过来了。 迷迷糊糊睡过去,大概到四点钟,又醒了,怎么也睡不着。是因为换了一张床吗?或是因为外面有水滴声,当当当敲下来,孤苦伶仃。那天收到表哥的包裹单,心里忐忑不安,是什么呢?不会是一个大包吧?还好,不是。里面装着我的读书摘要,一封信,另外还有有两支 新钢笔。笔记本是1998年夏天的,自己钉成,最后一页有句话说:“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对那些摘要本身好像是一种嘲讽。还有《增广贤文》里的箴言:“人情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有冷时。”有看破了世道的豁达,也有对事变人非的悲伤,隔了十多年,读来别有一番滋味。信里说,不可能忘记所有的一切,只是在等待“时过境迁”。是的,是。有钢笔可以用,太好了,绝对不是一笔勾销,两笔。我随即灌上墨水,把以前用的那支洗洗收起来。这一支写字很顺手,我天天随身带着,采访韩正市长在闵行校区的演讲就是用了它。我也想给表哥回一封信,只是,那些感谢 和歉疚能用笔写出来吗?再说。 天亮后我又睡着一点,不过很快被闹钟惊醒了。嘉硕起来上卫生间,我和他打个招呼。没有刷牙,我洗把脸就出去了。外面阳光明朗,我更看清了小区的破败的模样,没窗的房屋就像被挖去了眼睛的骷髅。再回头看一眼横幅,“早搬迁早得益”还挂在半空。不久的将来,嘉硕住的房子将会消失,我在这里呆过的两个夜晚和曾经有过的玄想,也会被掩埋在废墟底下吧。
2009.5.7~5.12
小区一角,2009年1月
笔和本子,200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