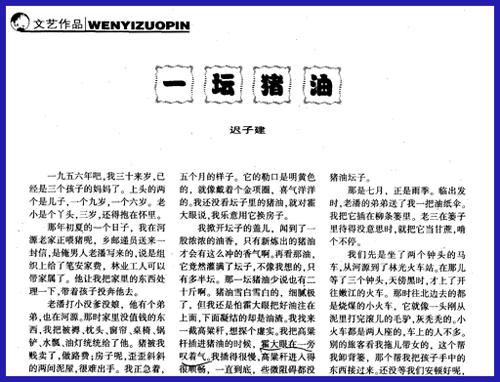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丰腴的猪油滚圆的坛 ——读迟子建小说《一坛猪油》 ( 返回 )
打开迟子建的小说《一坛猪油》,看到主人公千辛万苦抱着一个猪油坛子赶路,我想最后一定是坛子摔碎了,就赶紧往后翻着找结局。其实我只猜对了一半,坛子确实碎了,却不是在最后。作者几句话就交代了事实,然而故事的着力点并不在这里。相对于“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来说,坛子的破碎只是开始。 确实是一口好坛子。霍大眼提出用一坛猪油换“我”家的房子,且不说猪油怎么样,单是看到坛子,“我”就满口答应下来了。它像怀孕四个多月的女人肚子,浑圆光亮,带着股勾魂儿的劲儿。客栈老板对这坛子简直是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价钱随便开,大马随便挑,啥代价都舍得付。他把坛子比作女人,甚至看得比他老婆还要重,可以放在心里惦记着。老板的老婆为这件事大为光火,不惜自伤;后来,她还下跪求“我”成全老板,但“我”还是没答应。这一面是因为“我”着实喜欢这个坛子,另一面是因为霍大眼再三叮嘱,只能自己吃,不能给别人。 坛子碎了,“我”很看得开,当是太美的东西命薄;而且,猪油还可以刮起来,盛回去慢慢吃。在腥荤缺乏的深山老林,猪油炒出来的野菜是上等美味,“我”丈夫老潘乐意吃,他手下的林业工人也喜欢。老潘甚至不舍得拣出菜里的蚂蚁,因为那是坛子摔破时他们钻进猪油里的,浑身浸着油,挑出来可惜。我很快怀上孩子了,肚子格外明显。孩子生下来,小名就叫蚂蚁,老潘说,那是因为他受了蚂蚁的滋养,才会精血旺。这坛猪油是好东西,延续在蚂蚁的生命里了。 故事的拐角出现在坛子破碎的时候。前来接我的崔大林招呼“我”把猪油刮起来,里面本来有个绿宝石戒指,趁“我”不留意,自己藏着了。后来,崔大林靠这个戒指追着了程英作媳妇。人以物贵,找着这句话了。崔大林在戴着戒指的程英面前特没自信,房事都做不好,两口子一直没有孩子,熬中药喝也没用。一天程英洗衣服时不小心把戒指弄丢了,怎么也找不到,整个儿的人变得失魂落魄,再也没了以往的光彩;过些日子,居然连命也搭上了。 一天,蚂蚁网上来一条大鱼,“我”在鱼肚子里发现了程英丢失的绿宝石戒指。拿去还给崔大林,他死活不肯收,于是蚂蚁就留着了。直到老潘死后,崔大林才告诉“我”戒指的来由。他以前不肯说,是怕在老潘前边没法做人。崔大林因为有戒指而赢回了媳妇,但不是自己的终归不是自己的,他后半辈子都因为这过得不踏实。当初没有这个戒指会怎么样?生命不像搭积木,可以多次尝试,过去了就结束了,没有假设。 坛子,猪油,戒指,它们原本是一体的,因为“我”从马背伤摔下来而一分为三。都是霍大眼对“我”的一片心意。在“我”即将远别离之时,他几乎倾荡所有向“我”示好,却那么含蓄,并不点出来。看到“我”用高粱秆子测试猪油的好坏,霍大眼在一旁叹着气。难怪呀,那么不领情,就像明珠投暗。坛子是一颗爱情的种子,可惜温度水分不对,没发出芽来。待到“我”明白个中原委,霍大眼已经死去六七年了。世事多变,谁能说得清楚。 最叫人牵念的是蚂蚁。他受着猪油的营养来到世界,又带上绿宝石戒指不辞而别。可以设想的是,他到河对岸去找心爱的苏联姑娘去了。蚂蚁长得高大壮实,是“我”和老潘的骄傲。年老了,“我”听到鸟叫也像“苏生”,那是蚂蚁的名字。 小说有七页长,读起来觉得很顺溜,一会儿就完了。故事围绕这坛猪油展开,脉络清晰,没什么旁逸的枝节。读完之后,最深的印象是饱满。那坛子滚圆放光,那猪油纯净肥腻,那戒指透亮醉人,无一不是出奇的美满,无一不让人欢喜赞叹。字里行间充溢着人情之美,质朴清新。在大板汽车上,人们看“我”拖家带口,把最好的地方让给我。崔大林在船口等“我”一个星期,也不急不恼。鄂伦春猎人把“我”和崔大林送回家,丝毫不见外,就像对待自家人一样。崔大林结婚那阵子,林场的人都过来庆祝,女人们做菜,男人们喝酒,孩子们玩游戏,好不热闹。小说容下了跨距若干年的故事,节奏轻缓而叙述密实。它像一只熟透了的蜜桃,通体鼓胀,透着亮,一掐就会冒水。 故事是透过主人公“我”的眼睛看到的,一位性情坚韧、心胸开朗的普通妇女。通篇这么说下来,没有一惊一乍,没有大悲大喜,都平平常常。桩桩小事读来自然,平淡,读过之后却觉不时飞过神来之笔,耐得寻味。“可是那个猪油坛子可怜见的,摔碎了。”折腾了大半程,就这样把坛子的事情放过去了。她说她家老潘:“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事坏事都不爱跟女人说。”嗔怪中带着夸耀的意思。路上非常辛苦,老潘却不去迎接,她打算不跟他睡一个被窝,晾着他;事到临头,“看他哪里都亲,最后还不是睡在一起了。”浓浓的爱意,用几句话就对付过去,叫人过目难忘。她说猪油里的蚂蚁“贪了口福不假,小命却是搭上了”,说“人家都说崔大林很不高兴他和程英一起工作”,都包含着对生活的深刻体察,确实是那么回事。 活泼通畅的语言仿佛是从东北土地上长出来的,闻得到猪油味,闻得到冰冻味。衣服的后背被雨潲湿了,我怕有些不认识的花会药着她,高鼻梁和上翘的唇角随我,她长得才俊呢,自打程英结婚后……这些话有着强烈的北方特色,精准,传神,熨帖,读来很有满足感。也难怪,这么读着读着,小说就结束了。 生命饱满,故事饱满。除此之外,小说好像还有种说不出的好。是短小篇幅包纳复杂人生故事的举重若轻的姿态?是通篇用平滑节奏叙事而滤去议论抒情的洒脱?还是作者与主人公互成你我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读《一坛猪油》的同一个晚上,我读到了迟子建的散文《鹿皮袋里的劈柴》。她谈到的是左拉、毕加索、马奈、罗丹、大皇宫、香榭丽舍大街、奥赛博物馆等人和物,相对小说里那位身份低微的乡村妇女,迟子建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也是非常让我疑惑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行不悖,她如何能做到? 不管怎么说,迟子建做到了。她在小说里呈现了饱满的人生,透过她的散文可以知道,那只是大千世界的一种活法。行文的过程让她的生命变得层次更加丰富。
(《一坛猪油》,原载《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5期,2008年第18期《新华文摘》转载;《鹿皮袋里的劈柴》,发表于2009年3月4日《文汇报》笔会副刊。)
2009-3-8
迟子建和《一坛猪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