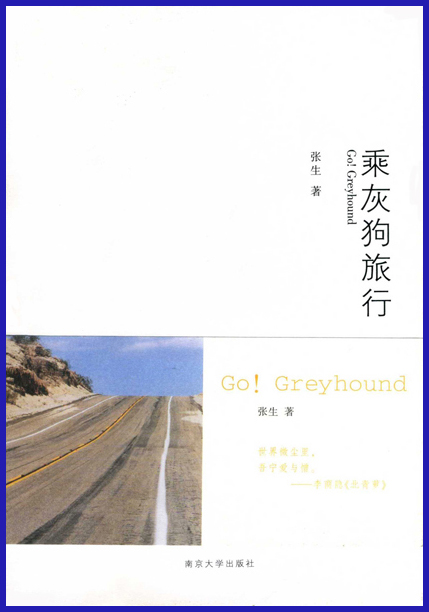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乘灰狗旅行》读后(二题) ( 返回 )
捕影成梦
除去腰封不说,《乘灰狗旅行》整本书简洁朴素,不含一点彩色,不设一幅插图,甚至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这暗含了正文九篇随笔的风格,低调,含蓄,利落。腰封是呈现给陌生读者的阅读指南,在方寸之间展示出全书精粹:波德里亚的公路摄影,英文书名《Go! Greyhound》,署名张生,还有李商隐的诗句“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山坡公路与Go(旅行)相对应,天高地阔,前方的旅程充满变数也叫人满怀期待。Greyhound(灰狗)是美国一家全国性长途汽车的名字,乘坐灰狗车旅行非常便宜,也便于观光。如果读者知道这层意思,则能窥见书中的异域风情了,都是张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访问学者时候的事情。两句诗可以看成作者的自况与真情告白,静悄悄地观察,静悄悄地体悟,静悄悄地把万般感情付诸文字。 展读全篇,不难理解作者援引李商隐两句诗的意图所在。不带什么野心,去除烟火气,心平气和地面对世界,面对周围的人和事。生活的本质在哪里?作者无意深究,他要做的只是忠于内心的本真感受,关注当下。《向左转,向右转》中,我跟着邓师傅学开车,第一次他莫明其妙地发脾气,第二次态度尚好,只是有点不安地翻看手机。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和邓师傅之间始终隔着一层墙,他教训“我”的时候,“我”非常不服气,但并不发作出来;“我”坚持己见甚至有所冒犯的时候,他反而非常谦卑。两个人的力量此消彼涨,拉锯一般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不过,这些都是“我”的感受和猜想,邓师傅的体会则完全不可知晓。“我”看到他三番五次地摇晃水壶喝水,只是看到了而已。生活有本质吗?作者没说。如果有,未知性将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吧,近在咫尺的邓师傅都让“我”觉得难以理喻,遑论漫无边际的大千世界? 说实话,显然,我想,很可能,看样子……这样的表述在书中随处可见,《乘灰狗旅行》是一部私人叙事的文集,一点也不回避“我”的固执。世界如何,都要通过“我”——也就是李商隐诗里的那个“吾”——的观察体悟,这是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点。《大站车》说到,“我”觉得纽约就像家庭旅馆老板谢经理:含蓄而矜持,对一切事物都保持平静而超然的态度。这是不是偏见?不是,绝对真实,因为这是“我”亲身感受纽约之后留下的印象。其实无所谓正见还是偏见,每个人的心灵感悟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很宝贵,也都值得珍视。有了“我”这份口无遮拦,读者很容易换位思考,体会到“我”的无奈和尴尬。谢经理“嗯哼”个没完没了,很有美国人的腔调,“我”多次从言谈中捕捉到他的上海话口音,试图确认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得到他的回应。是不是“我”自作多情了呢?在三藩市,一位金发妇女看到“我”T恤衫上的时代广场图片,主动表明她的纽约人身份,她不觉得难为情,“我”也不觉得她冒昧。有的人喜欢坦诚,有的人倾向封闭,生活就这样无比吊诡。 不能不佩服张生驾驭文字的水平,顺滑流畅,如同现场直播一般记下生活的轨迹,却又不显卖弄。这些随笔可以当作小说来读,以第一人称叙事,内中弥漫着“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的诗的韵味。用以命名集子的这篇《乘灰狗旅行》把一段穿越荒漠的寻常旅行写得摇曳多姿,将下车时乘客老马却意外被人捅死,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作者保持了极大的镇定和克制,寥寥几笔带过,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生活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纵览生活全貌永远不可能实现,文中的“我”也未必有这样的企图;作为作者的张生则是悲悯的,他耐心收集生活的碎片,捕捉现实的影子,力图用文字再现那些曾经发生而已经远去了的梦。一个个梦借着书的传播飘向读者,带去 悠悠的思考和绵绵的慰藉。
(注:此文主要为书中《向左转,向右转》《乘灰狗旅行》《大站车》三篇的读后感。首篇《星期天》两年前初读于《收获》杂志,文字记录见于《遇见张生》第一部分。)
2009-3-14
放大了的世界
好的文字会有一种神秘的启发功能,它让读者感到,不光是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下增添新的材料,而且能够扩充思维的边界,发现并确认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好的文字甚至可以打破读者原有的认知图景,建立新的参考标准。《乘灰狗旅行》便是这样一部作品集,对得起好的文字的称号,不仅提供了异于时闻众说的观点,而且把这些观点的来由清晰展现出来,用一种感性柔软的方式,带领读者走进独特的地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内心世界。 美国,加州,拉霍亚。作者张生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以此为据点,游走四方。加州的阳光很好,连续几个月碧空无云,这让习惯了上海阴雨天气的“我”非常不适应, 呆了没多久,皮肤就晒得乌黑。高大的棕榈树,哗哗作响的桉树。坐半小时公交车再走一段,可以看到大海。乘灰狗车去芝加哥,沿途单调荒凉,毫无景致可言,以至于过后“我”再也不想乘灰狗。买票排队登上著名的西尔斯塔,索然寡味。“我”对纽约的印象很一般,如同一位家庭旅店老板,含蓄矜持。洛杉矶 整个儿像块破抹布,那里的华人超市跟中国的差不多,只不过商品标牌上多了一行英文。对“我”来说,这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美国,也不是原先想象中的资本主义的美国。游历的过程同时是获得新知、去除偏见的过程,尽管“我”本初的意图 不完全是这样。 访学的日子让作者陷入了巨大的孤独中,经常一天到晚都没机会说话,为了解闷,他有时专程到热闹地方的咖啡馆去,坐下来看周围的人,发呆。有机会与朋友、老乡、教授等各层面的人接触,便将这些 交往感受写下来。虽然这里面有张生本身愿意写、擅长写的因素,但可以相信,无处不在的孤独是将一段段经历最终变为一篇篇文章的催化剂。在孤独的映衬下,琐屑的事情也变得有滋有味,值得再三回想。作者的观察灵敏而犀利,感知人情往来的温度,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到当地生活的内核。由此,一己之经验有了文化标本的意义,经 过文字的保存与传递,片刻的感受也被赋予了永恒的内涵。 这是一片被作家放大了的世界,读者可以借助文字的引导,进入曾经发生的悲欢故事,感知内中的人情冷暖。校友王老师酷爱语言学,定期到图书馆去阅读,“我”为了和他谈话,还专门去翻阅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文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店 铺里售卖盐水鸭的人正是王老师,不免大惊失色,躲在一边生怕他认出来;过了些日子,又和王老师见面聊天,临别时他却大大方方地送了“我”半只盐水鸭。“我”一直都在疑惑:是不是因为那天王老师看到了我,才来送我盐水鸭?(《校友》)这里有“我”的躲避,可能也有王老师的躲避。 同样的主题在书中多有出现,《大站车》中家庭旅馆老板竭力躲避他的上海人身份,《自助餐》里参加医学实验的双胞胎弟弟似乎不愿意认出有过一面之缘的“我”。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最后一句说:“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这种躲避是因为单纯的金钱关系,容易理解;张生笔下的这些躲避则情况微妙,可能是对方在刻意保持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感情认同,可能是他们不想暴露个人隐私,也可能一切只是“我”的不着边际的猜想。 宗教信仰、两岸关系、文化差异这类宏大的命题在集子里都有涉及,不过作者是用了微观叙事的方式,唯其如此,故事的肌理格外细腻,而且富有个人魅力。李梦龙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坚持认为是台湾人,“我”开始觉得诧异,后来理解了,因为他不希望被没有差别地代表了中国。(《欢迎你到上海来》)“我”慢慢理解的事情有很多,包括博德恩何以有志到甘肃传教,爱娃何以在查经的场合大谈特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自己所遭受的迫害,还有经书里的那句“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希伯来书》)尽管在美国的生活让“我”觉得充满了错愕、误解、无奈,作者还是多次展现了经由沟通而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华人在美国的境遇是《乘灰狗旅行》一以贯之的主题,因为九篇文章都是“我”的亲见亲历亲为;但书中还有两篇文章集中谈论他者,那便是《星期天》和《冰水》。温情脉脉的叙述语调与他们黯淡破落的国外生活相并置,格外发人深省。 《星期天》的主人翁张清是剧作家陈白尘的关门弟子,在校时才华横溢,曾引得众多女生趋前搭识,他还潇洒地宣称“四大名著就是四大糟粕”。在美国的日子却窘迫极了。他苦苦地研究《水浒》,写了一些文章,然而并无惊人之处,只是一些读后感而已,“在我看来,意思并不大”。他试图在孩子面前保持尊严,却不见得成功,甚至当着“我”的面责骂孩子,有失待客之道。高速公路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堵,百威啤酒也不见得只有美国下层民众才喝……这个张清,多少活得有点委琐,尽管“我”没有直说。 《冰水》里的叶老师在比较文学界享有盛名,但他并不借助地利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相反对中国古典文论情有独钟。不仅学生私下里说,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套东西并不怎么受欢迎。但即使只有十个学生,叶老师还会用出全副精力,对着大片空椅子慷慨激昂。他自己忍不住念叨,在北大开讲座的时候有几百人听,教室阶梯上都坐着学生。风光不再了。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史差不多已把叶老师忽略。大陆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他天真地期待受邀前去参加新书发布会,实际上出版社不仅没有组织发布会,连他提出的把稿费折合成美元的愿望也没有满足。叶老师生活在被他汉化了的美国,用“我”的眼光看去,尽管他学厚名高,却未免闭塞寂寥,那种生活实在不是最佳的选择。 九篇文章里,“我”自始至终是在场的,而且前后形象少有冲突。透过零散的记述,读者大致可以勾勒出“我”的样子:学者、作家,毕业于南大,爱好西方文论,访学时三十六七岁,工作关系在上海交大,妻子、女儿都在上海,如此等等。这确实是作者张生的个人情况。如果把文中的“我”虚化一下, 这些随笔也可以当成小说来读,故事圆整,文气贯通。“我”性格内敛而真诚,作风正派,交友广泛,勤于学习研究。当然,“我”并非全知全能,经常会心存疑惑、感到焦虑,乃至陷入沉思,自问的句子在书中随处可见:的确,与上天和浩瀚的星空相比,人这种造物究竟又算得了什么呢?实际上,我何尝当过美国人呢?但是,这和在中国生活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想法很怪,是不是?!诸如此类。 文字是感情的外射,放大并固化了现实。透过这些作品,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张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的见闻感受,看到从圣地亚哥辐射开来的美国的风土人情,还可以看到“我”在彼时彼地看待事物与处理问题的方法,亲近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附记 周日逛文庙旧书市,其时已读文集中前四篇。遇见夏中义老师旧版著作《艺术链》,开价十元,八元拿下。在一书摊翻看2008年《作家》杂志,不期看到张生的名字,又见刊中《冰水》,疑该文已收入书中,但不确定。六元两册,摊主不肯还价,犹豫后最终购买。回来一看,果然已收在书中。 年初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张生老师写的《一苇渡江播华音——记诗人叶维廉教授》,后来我向张老师提起这件事,他说:原先很长,删成了这个样子。毫无疑问《冰水》里的叶老师就是叶维廉教授。报纸文章对叶教授褒扬甚多,也对他如何看待中西文化方面略有疑惑,似与《冰水》相承。
2009-3-18
《乘灰狗旅行》书影(含腰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