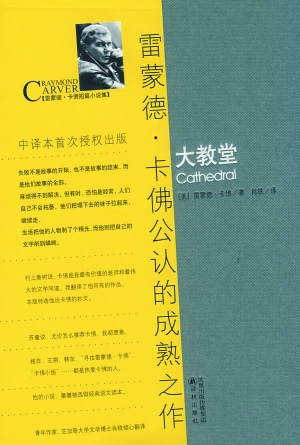|
我的小屋 我的简介 我的爱好 我的文章 我的摄影 我的印章 我的音乐 友情链接 与我联系
“真是不错” ——关于《大教堂》的碎语
( 返回 )
(一)
盲人来我家访问我妻子。这故事简单得一塌糊涂,出场的是三个人,时间大约一天,地点在我家。作家的本领在于把故事充分展开,风生云起,让人读来有滋有味。 我对盲人的到来并不怎么欢迎。顶多,那是妻子的事,我懒得理会。有什么意思呢?当初妻子和盲人有过一些来往,为他读报,后来分开了。他们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相互寄磁带。妻子对此兴致很高,甚至为他写诗。两个人的亲近简直叫我生气。盲人要来我家,来就来吧,不关我的事。 这盲人着实可爱。他有说不完的话,对什么都有浓厚的兴趣。头一回握手就说,好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嘴上仿佛抹了蜜,一口一个“老弟”。我要给他搬箱子,他说不用,自己来,别客气。吃饭的时候,他吃得那个香呀,吃肉,吃土豆,吃面包,喝牛奶,喝酒,都津津有味。还一起吸大麻,看电视,干啥有干啥的乐趣,生活无限美好。 空气里飘浮着某种怪怪的味道。开始大概是醋意。妻子有过前任丈夫,一位青梅竹马的军官。那个夏天,妻子给盲人读报,分别时盲人摸了她的脸。咳,摸了妻子的脸。我对盲人的来访不冷不热,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后来就有点暧昧了。妻子坚持给盲人铺床,跟他说,什么时候要睡了就叫醒她,她去铺床。当这是待客之道。面对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我禁不住得瑟起来,妻子是我的,不是你的。妻子的睡袍滑落,露出一段多汁的大腿。看,多么诱人!我不想让盲人看见,把睡袍拉起来。盲人当然看不见,要看也只能自己看,于是,我又把睡袍给掀开了。 假如说事情有转机的话,那也是悄悄发生的,神不知鬼不觉。电视上出现了大教堂,我向盲人描述。在他热情的感染下,我只能这么做,也乐意这么做。他什么都看不到,没办法。哪里有雕塑,哪里有壁画,很高,很大。我说不清楚,还是说了,不管有用没用。盲人的话就像巧手木匠做出来的卯眼,紧密衔接在我留下的榫头上。哦,画一座大教堂吧。找来纸和笔,一起画。盲人用指尖就能感受到效果:“画得不错。”后来,他的手扶在我手上,感受我闭着眼作画的过程。 大概就是因为那手指传递的体温,阻隔在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冰冻悄然融化了。春天已经到来,这多么叫人欣喜!盲人叫我睁开眼,看看画得怎么样。我沉浸在这种充满温情的氛围里,哪怕闭着眼,一样可以对大教堂的画作出判断:“真是不错。” 小说收得那么干净,韵味丰富极了!
(二)
小说里,盲人的妻子没有出场,作家给了她充分的理解:永远无法出现在爱人眼里,无法从盲人那里得到女人都想要的对面容的赞美。雷蒙德·卡佛就像孙悟空那样钻到笔下人物的肚子里了,对他们的所感所念了然于心。客厅是一座小型的舞台,三个人进行着节奏缓慢的演出。平平淡淡,又跌宕精彩。借助作家的细腻笔触,读者也成了观众,欣赏他们的表演,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读完《大教堂》,我的第一反应是路遥的《人生》,它的结尾也是用了主人公的一句话。高加林抓起两把泥土,大声喊叫:“我的亲人哪……”悲悲凄凄,留给读者宽阔的回味余地。《大教堂》的结尾同样十分耐读,不仅是“我”对刚画的大教堂的评价,也是彼时“我”对盲人解除防范完全接纳之感情的自然流露。当然,用来作为一篇简短的读后感,也是可以的,“真是不错”。我猜想,抱有这种想法的读者会有很多,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给他一把刀,译者就可以削铁了。已经十多年没见肖铁的名字。读高中时,班上不少同学订了《语文报》,我们经常读到肖铁的文章。他还小呢,是个学生。他老爸肖复兴有作品入选初中语文课本,很牛。我们从鲁慢、巴铁这些名字里看到了肖复兴对儿子的期望。等我拿到《大教堂》一看,啧啧,青年作家、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肖铁翻译的,我就想,此肖铁可能就是彼肖铁。待我到网上一查,可不是的。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肖铁他老人家居然和我是同龄人。 肖铁的翻译读上去很舒服,文句优美,字词洗练。他很少使用生僻的词语,却一样可以做到精准生动。比如盲人和我一起画大教堂的场景:“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盲人和“我”之间那层亲密的关系,用一个寻常的“骑”字就活龙活现了。再如雷蒙德·卡佛自话中的一句:“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多么轻松,可是传神。肖铁设置了作者自话这么一个板块,也是很可称赞的,对我这种以前从未读过卡佛小说的人来说尤其有必要。那仿佛架设了一座跨越时空的长桥,带读者来到作者的近旁。至于读者如何达到卡佛的内心,那就要靠一篇篇的小说了。 卡佛生活贫苦,为生计所包围,甚至大部分的作品只好在一次坐下来的时间内写完。他不能像路遥、陈忠实那样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大部头,只能作短小的急就章。小说是他卑微生活的记录,同时也是智慧和才华的凝结,是对卑微的淡化与超越。凡俗生活里的一个个场景成了他的写作资源,信手拈来, 富足充盈。卡佛对生活的不屈精神和他的小说才华一样让人肃然起敬。
(三)
自话、译后记都写得很好,颇有一些句子可以记下来长久存留,比如“陈述的基本正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还有“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等等。读过村上春树的序言,我就一篇一篇小说往下看了。 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样好。前面十一篇叫我觉得疲软拖沓,劲头不足,我是费了好大的耐心坚持读下去的,记不得故事情节,甚至篇名。可能哪里有问题。阅读体验的改变出现在最后一篇,用来给集子命名的这篇,让我猛然打了个激灵:不一样,有意思。隔膜与理解、冷漠与温情都不是绝对的,《大教堂》呈现了微波荡漾的转化过程。读完之后心里非常舒服,还想再读一遍。后来我在卡佛自话中看到他说这篇是例外,写故事对他来说是一个自我展开的过程,更萌生出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最初让我接近《大教堂》的因缘是张新颖发表在《文汇报》笔会版的一篇文章,名叫《写这些被生活淹没了的人》,挺长,分四个大的章节。文章最后说:“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确实好,身手不凡,于是我急匆匆地找到《大教堂》,买了回来。当时并没有留意这是卡佛的话。读过小说再回头看张新颖这篇文章,心里不由恼火:这个大坏蛋,多少句子段落是直接或间接引用了雷蒙德·卡佛、村上春树还有肖铁的,她到底想说什么? 《大教堂》的腰封上印着好几段煽情的话,角度各有侧重,说白了就是让读者掏钱买书。卡佛的小说是好是坏,这个见仁见智,腰封上的话并非定评。作家邱华栋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说:“对眼下神化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要警惕——他才气远不如约翰·厄普代克,仅就短篇小说而言。”也够狠毒的。 别人说好也罢、说孬也罢,我觉得《大教堂》还是值得一读的。那会有一种和作家进行心灵对话的感觉,真的不错。
2009-2-24
(发表于2009年3月30日《上海交大报》第四版 ,署名若何。 责任编辑:杜欣)
《大教堂》书影。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
|